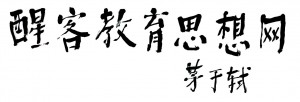演讲者|董云川 时间 | 2010-05-15 地点 | 中山大学 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2010年会现场
我先回应一下刚才几位专家提到的问题,我们在很多地方谈大学理想、大学文化,经常就会有人问,你谈的问题能不能解决?我今天先亮明我的观点——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是两回事。提出问题有时候只需要一个人的智慧就够了,而解决问题常常需要依靠系统的、组织的力量!如果苛求所有提出问题的人都要负责去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就很少有人去“多管闲事”了。
至于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判断,我完全同意昨天有一位老师提到的观点——中国是高等教育大国而不是高等教育强国。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规模和教育机会方面所取得的业绩有目共睹,但是它的内在品性怎样呢?这依旧是值得怀疑的,也是值得追问的。所以涉及今天这个会议高瞻远瞩的“未来”选题,冯教授跟我预约发言的时候,我一再地推辞,原因就是我觉得再谈这个问题已经有点倦怠了,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是因为太重要所以推而不动。后来我申请讲一个形而下的相对具体的问题,冯老师又不同意,于是我还是努力从宏观的角度反省一下中国大学品质不高的根源问题。结果昨天一天听下来,我觉得“上当”了,因为许多大专家还是选择了小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只适合在课堂里面对学生的时候“讲解”较为妥当。在冯老师的敦促下,我试图梳理出制约和削弱中国大学品质的几个绕不开的问题。
站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百年的转折点上,前瞻后望,发现如此人口众多的大国,始终未能直接产生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我认为这仅仅是现象之一,更值得反省的问题是泱泱大国,与此相称的哲学家、思想者、文人、诗人们在哪里?还有多少?温家宝总理慈祥而富有责任心地拉着钱老的手,接下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而我的问题是:钱学森之问本来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只有人议论,没有人动作。致使大学品质平庸的游戏规则近些年丝毫未动。经常有人把我们这些谈精神、谈文化、谈问题的学者视为空想主义者,认为应该面对“现实”,随大流运作,大学就将越来越好。这是典型的集体无意识状态!如果大家都按这个渠道走下去了,当然高等教育在数量上的贡献还是会有,但是必将在“品质”上留下遗憾!禅宗有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骑着马,马跑得很快,旁边的人问他,先生你要到哪儿去?他说我不知道,你问马吧。我以为中国大学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我们高喊改革、我们谋求发展、我们不断解放思想,但是要到哪儿去?我们不知道。
1998年1月,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草坪上写完“找回大学精神”第一稿,当年就与北大一百周年校庆遥相呼应而问世出版,本书2001年第二版,2005年年第三版,到2008年刚好十年的时候,又有机会造访哈佛、耶鲁。有学者提醒我说,1998年你在美国西海岸找大学精神,今年从东海岸的哈佛耶鲁回来是不是应该出一本再找大学精神的书以为对比?我真觉得是个好创意,但最后无果而终!原因是我失语了,没有办法再深入下去。因为十年前的问题依旧顽固,而且大学不断“背道而驰”,离“文化”、“精神”似乎越来越远了!
回到我的命题上来,今天对“品质”问题阐述几个基本的判断。首先还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学飞教授昨天引出的话题非常好,要寻找迷失的本性。但遗憾的是,后来跟进的话题似乎偏离了这条线。大学本质上是文化组织,它有政治属性,也有经济属性,这一点没疑问。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都有政治属性,它要为国家服务,要为社会孕育人才;它同时也有经济学的属性,因为任何一个组织必须有投入、产出和效率的筹划安排。但是请记住,它的本质归属是文化。什么时候中国大学能够成为一个文化组织而不是一个准行政组织或者准经济组织的时候,中国大学才会有杰出表现。温总理语重心长地在“五四”青年座谈上谈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两招。一是要让教育家办教育,不是办一阵子,而是办一辈子。我的问题是,是谁让他们办一阵子的?这种制度是谁在安排、谁能够改变?二是要让文科学生读一点自然科学的书,理工科学生读一点人文的书。我以为这是微观技术层面的问题,不是重点。另一方面,谈到中国大学的问题,我非常欣赏彼得杜拉克针对亚洲金融危机说了一句话,叫做“亚洲金融危机的问题不是因为电脑用得不够,而是因为人脑用得不够。”这句话相当经典!所以现代化也好、信息化也好,这些“器物”和技术层面的趋势是势不可当的,你学不学、愿不愿意都迟早会卷入这个潮流。问题的根本还在于中国大学什么时候成为一个思想的聚集地,没有思想,操作什么样先进机器的人都可能是蠢才、庸才。所以说制约大学品质的首要问题是本性的问题。
第二就是制度安排的问题。我在2000年的时候撰文,指出中国大学、政府与社会之间形成一条不恰当的直线关系,而不是呈交叉互动的三角关系。大学在这边、社会在那边,而政府居中。凡谈适应,大都远离真正的自主适应,大都是政府教我们怎样去适应。什么专业可以招,什么专业不能招;什么时候扩招,什么时候紧缩;政府手把手教我们“适应”,然后又手把手教我们“创新”,这是很滑稽的事情!大学本来就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它会自觉改变、调整,并会寻找到适当的生态位存在下去。历史其实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西方大学的发展史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我们偏不这样做。当今无比强大的教育主管部门及其领导们执着地认为,我们不管你们就会失控。于是,大学就被剥夺了自组织能力,丧失了自主成长和自主调节的机制。因此才会在高等教育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出现对于大学办学自主权层出不穷的呼唤。所以在是否适应社会的问题上,并不是大学说了算的。在这一点上大学连菜农的自主性都没法比。一个菜农批发白菜,是因为白菜卖得起价钱,过两天有十个人挑来了同样的白菜,他自己就会转向了,并不需要组织规定他说明天可以放开卖、后天只能紧缩卖、而下个月严控所以不能再卖。不会的,他会自己会改变而适应市场的,但大学连这种自主性都变成了奢望。这个专业要控制,那个专业要放开,这种外部指挥内部运行的场景十分可笑。
在一个金字塔体系中,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立体互动的体系,而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总体上是一个行政主导的体系,大学只是这个庞大行政系统中的一个基层单位,分别被授予副部级、正厅级或者是副厅级待遇。在这个位置上,你就没有理由脱离组织部门、人事部门、教育行政部门以及诸多与大学运行相关的横向委办厅局的控制。这一点我算是想通了,所以对于所谓的制度变革暂时不存乐观的期望。
刚才的议论其实已经连带回答了第三个问题,就是自组织机制被剥夺。接下来的第四个问题谈到个体角色的混淆。我在哈佛访问的时候有个教授跟我讲,中国的教授和美国的教授最本质的不同,就是美国的教授比较“professional”,他们能够长时间专注于某一领域的研究,而我们却很难做到,并且我们的“全才”较多,不论是谁,到最后都要弄个教授、博导当当!我经常说,什么是硕导,就是一说就倒;什么叫博导,就是一驳就倒。主要的问题在于全面的角色混乱,比如学术官僚化、官僚“学术化”的泛滥。更是导致我们个体角色不能坚守的最根本原因。
第五个制约品质的问题就是关于所谓的“创新”。关于创新缺失的论断,我认为是绝对存在的。在现行的运行体制之下,平庸是必然,要是有创新才是奇怪。为什么?我1994年写过一篇文章,到现在16年过去了,当时提出:就创新而言,土壤比种子更重要。而创新的关键是什么?我常在讲座时告诉校长们,创新不需要喊口号,创新的本质是求异的,不是求同的,中国大学出现了品质危机、缺少群峰并举的思想家,都与创新土壤贫瘠有关。要谋求创新局面,其实非常简单,容忍不同就行了!无论何时何地,一所大学、一个学科、一个系部、一个组织如若能够容忍不同,这个地方一定成为创新的摇篮,成果必然层出不穷。谢谢!
现场问答
丁学良:大学内部本身也有保守性,如何看待大学的保守性,能否以北大人事改革为例,来破解一下大学内部改革的约束?
董云川:大学本身的保守性在历史上有特定内涵,它曾经或者偶尔也会在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时代潮流里封闭坚守,显示出孤芳自赏和固步自封。但这不是中国大学的问题。为什么今天我一直在谈机制问题,因为只要建立起开放的机制,任何的保守性就难以固守。因为保守就会被淘汰,保守就活不下去。近年来,也有人要求大学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但是就像有位专家所说的那样,中国大学从来就没有进入过象牙塔,所以还谈不上走出象牙塔。我的观点亦然,我们现在恰恰需要一点清高,可能反而有助于中国大学走向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陈学飞:北大2004年的人事制度改革,当时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接近西方大学制度的一种安排,是想打破中国大学教师的终身制制度安排,当时应该说绝大多数老师都支持这个改革。但是总体说我觉得是失败的,这是因为政治上的保守性导致的。后来实际上是北大的党委害怕,如果说我们执行这一套改革,当时估计可能会有一批年轻教授要罢教,而北大罢教确实了不起的,是通天的事情,就很难做,所以党委就主动把这个东西往后退,最后实际上并没有实行。
董云川: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实施受阻的原因是没有改上面。也就是说,那些管教师的人们并没有一个同样优胜劣汰的机制去筛选他们。我有一篇文章写到“教师不是被管理对象,学生不是被教育对象!”整个大学的运行逻辑包括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后勤资源等等,上位组织结构和运行逻辑都没改,只拿老师改来改去是说不通的。
听众:陈学飞老师说到,我们高校改革总是以适应为主导,从政府的角度是这么要求的。我的问题是,高校的立场是什么,我们有没有真正地去适应政府的要求,或者我们很愿意真正地去超越,现状好象我们既不适应,也不愿意超越,这一点你们怎么看?
董云川:经常听说教育主管部门批评一些学校盲目升格,后来有一位明眼的专家指出:当前中国高等学校竞相升格的行动都不是盲目的,恰恰是有目的的升格。这种现象就是游戏规则引发的“适应”。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大学很难形成自己的传统,因为需要不断“适应”外部。
信力建:在目前的条件下,中国的高校改革是没有办法完成的,要拆这个梁或者柱子来改革,这个大厦就会倒下来。我觉得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引进外国的大学和私立大学,在楼的四面建很多的柱子,把这个楼重新撑起来,才能够把原来的这个大学建筑改掉。当时搞高校合并和扩张,把中国高校再一次彻底毁坏。1952年搞过一个院系调整,是按照苏联的模式调整,那个时候就应该可以开新的大学,原有大学保留,那时候还有机会,但现在一点机会都没有了,这个观点你同意吗?
董云川: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利益格局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大学改革的最大问题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既得利益问题。所以多元化教育格局形成的障碍,并不在于非国有的教育力量是否强大,而在于让不让你平等角力的问题。
董云川: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