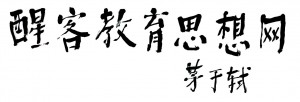作者 | 陈岚 发表时间 | 2013-02-15 来源 | 微信公众号“女拳”(作者授权本网)

她把我塑造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也许是从臭气熏天的鸡窝里掏鸡蛋开始。也许是在集市上卖鸡蛋,昂着头冷笑的那一刻开始的。世俗的太多东西,在她那里被蔑视。所有的行动,在她那里,都是简洁的、直接的、明了的、实用的,所有的目的,也都是高尚的、纯粹的、和光明的。
我的母亲是条暴龙。
我,已一大把岁数、牵着抱着自己的孩子了,也算混得不错,但,在妈妈这条暴龙面前,仍然不能放松。过年回家,她眼睛一横过来,我心头一紧,马上电脑自动扫描式地自省一遍:衣服穿得不合适?鞋子没擦干净?该赶紧去收拾桌子?厨房里还有啥活该我干的?赶紧该干吗干吗去,迟了,老太太就发飙了,等她说出口时,一定没有好声气儿,不是哧地冷笑,就是吼叫。难得她慢言细语地给我说个事儿,我我我简直受宠若惊。
自己还没有孩子时,一再地发誓,如果我有了孩子,我一定一定会好好地对待她,不会打她不骂她不恐吓她,爱她,爱她,全部身心地去爱她。象穿越回过去,爱那个被母亲留在寄养家庭的自己一样地爱。
一岁左右,我曾被寄养在镇上一个专门带孩子的女人那几个月。那段日子必不美好。听说,一个邻居顺道去看我,幼小的我竟然认出这个邻居,扑上去死死抱着她的腿,嚎啕大哭决不放松,因为知道,她是能带我回家的“故人。”
自己有了孩子后,对这一段过往,不能释怀。那么小啊,你们怎么能就把我丢弃在别人那里呢?我盯着饭桌对面的爸爸妈妈问:“为什么?”
“两个孩子……带不过来……”他们互相对视了一眼,嗫嚅着回复。
“那为什么不是把哥哥送去给别人带?我小一些,更需要照顾才对!”不依不饶地问。
难堪的沉默和无力的辩解。我问完也就算了。问完,说完,就是我最大的谴责和反抗了。他们也知道。几分钟后妈又开始象暴龙一样吼叫:“赶紧吃,最后一个的洗碗!”
妈妈不喜欢我。妈妈喜欢哥哥。妈妈是非常难以讨好的。无论我做什么,她都不喜欢我。这是从小到大的记忆,奴隶背上的鞭痕般清晰,深到骨髓,深到潜意识。有一次,一个小木桶放在跟前,我和哥哥面对面坐着泡脚,他拿热水壶添水,手一歪,一壶开水浇在我的脚面上,我尖叫起来。妈妈正在院子里和人说话,闻声跑进屋,二话不说,先重重抽了我一嘴巴。
“你出生时就是个忤逆不孝的家伙!”妈妈最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八个月时胎位还很好,到临产了,你变成了屁股朝下,臀位产!疼了我一天一夜也生不出来,差点死了!”妈妈还要狠狠补上一句:“我跟医生说,把它扒拉出来,死的活的不管!”
听了很多遍,并不会因为听得次数太多便麻木,每听一次,都血腥淋漓地战栗。
妈妈铁齿铜牙,个性凌厉。人人都说我口才好,其实我妈妈说话,那才是钢板钉钉,又狠又硬。我从体制内辞去优渥职务,成了一个落魄书生的日子里,妈妈吵:“就你?就你?你能写得出来,眼睛都扒出来给你!”沉寂在家的日子,家里有庭院,院有间小屋靠马路,她指着小屋,要爸爸把屋子开一个门面出来:“送她去学理发!学个手艺,回来开个理发店,好歹也不吃白饭。”我就想起高中的日子,她不看好我读书,跟爸爸说,县城宾馆在招服务员,还是事业编制,不如送我进去当服务员。我可是她“三岁赋歌、七步成诗”的神童女儿!还记得爸爸看着妈妈哭笑不得、匪夷所思的表情。
妈妈可不是没受过教育目光短浅。她是60年代高考没废除前,罕有的女大学生,毕业于解放军军内名校。她自己尝过读书艰苦,我外婆重男轻女得厉害,女儿成绩再优异,也舍不得每年开学要交的几块钱伙食费——那时候中学似乎不交学费,要换在今天,妈妈天资再好,也断然没可能读书。每逢开学,妈妈必定要又哭又求又闹,每每要下跪,才能从外婆手里要来那几块钱去镇上上学。学校打饭,她到了周末就不吃饭,将打下来的每天四两米凑起来,装在罐子里,提着走几十里路回家,给全家人吃。高中毕业时她可以读更好的学校,但为了立即拿钱,报考了军校。一进学校,发了当月和下月的2个月生活费,50元6毛。她留下6毛钱零用,50元整数邮寄回去。
妈妈不喜欢我有很多理由。馋,懒,贪玩,调皮,嘴犟。军人出身的她对孩子的教育只有“命令和服从”,教育方式只有“规训与惩罚”。对超出生存需求之外的一切肉体需要,都抱着极度轻视。比如,零食在她眼里是罪恶,睡懒觉那就是道德堕落,贪玩是不可宽恕的,爱穿好衣服是虚荣,去理发店剪头发是小资——劳动、劳动最光荣!于是我5岁就是个好腿,打酱油、买面条。机器压制的面,流水一样从机子上淌下来,师傅用手一捞,齐刷刷地断开,秤出2斤,我交上粮票和钱,放进一个铁丝编织的小篮子,走过3座小桥,回家。家里有一个小铅皮桶,我可以拎得动,提桶下河去打水回来,一趟一趟地跑,也能提回来半缸水。
有一次的打非常暴烈。我和哥哥煮饭,在煤球炉子上,饭焦了。害怕打,我们俩一商量,把饭全刨出来倒给鸡吃,重新煮了一锅。结果妈妈一回来就闻到焦味,鸡窝里一看剩下的白花花米饭,拖过来就一顿毒打,边打边骂边哭:“作孽、浪费、坏东西,养你们有什么用,不如生下来时就一把捏死!”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样的威胁非常真实,不听话,就捏死、摔死、淹死……
那时候住大院,我们家打孩子很有名的。邻居看到我,我手舞足蹈地玩着说着笑着,给别的孩子讲山海经时,一个阿姨经常是劈头笑笑地问:“今个又挨打?”我不喜欢他们,这些带着诡笑的成年人。也听得出他们的恶意。但自己是心虚气短的:被打,总不是个光荣的事。孩子再小也知道,不被父母宠爱,走到哪里似乎都矮人一头,就讪讪地不说话了,走开。
街头已经流行各种时装,但我母亲以她的少女时代的审美标准和生活标准来要求我。要么是旧衣服改改,要么是她自己在缝纫机上用棉布做一套——我是全班同学中穿得最老土破烂的那几个,有一次,我过年的衣服是在旧衣服上接了一圈边儿——还是色差极大的——这对于一个敏感好强的孩子,简直是最大的折磨。对我们的抗议,母亲轻蔑地说:“我们那时候连衣服都没得穿,不也考上了大学!”有时候还会上纲上线:“就是要治治你的虚荣心!”
不管怎么样,孩子总会长大。生命的激流按照自己的意志,一路磕碰跌宕,也奔向了原野。没有被母亲温柔呵护过的孩子,心灵是有创洞的。我一直在伴侣身上寻找无条件的爱与包容。是的,我要求没有条件。一旦有挫折,我就毛发皆竖,刺猬一样狠狠地去扎对方,并会立即萌生退意:“我不要你了!”一切的一切,都是母亲对待我的摹本的复制。性格强烈、男性气质突出的异性从来都立即被我拉黑名单,我只选择温厚和善、带来安全感强烈的异性交往。心理学意义上来说,我是在寻找一个“阉割后的男性”替代母亲,透过情感关系来解决内心的焦虑。
和暴龙妈妈的战争,一直在继续。她不接受我,尤其是越来越叛逆、我行我素的我。我也恨她,因为不管我做得多好,她都嗤之以鼻。有了孩子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愤怒尤其高涨:“小生命多么脆弱可怜,当年的我就这样小,你们竟然这样对待我……”就像憎恨那些虐待孩子的人一样,不能原谅曾经年轻的他们,这样对待孩子。
直到如今。一个早晨,本经历了一个无眠的彻夜,挣扎着起来给uu做好早饭,面包、果酱、煮鸡蛋、煎肉卷儿、红薯稀饭。uu懒懒地咬了一口面包,就丢在碗里,新榨的果汁看都不看一眼,又开始找借口不吃早饭:“妈妈,我肚子不舒服……”我忍无可忍地爆发了,指着她吼:“信不信我把碗给你砸了?!”
被呵斥的孩子眼泪汪汪,不敢哭,含着泪小口小口地啃早点。在她眼里我一定象个恶魔。我自己跑到卧室,把门关上。充满了失败感。我发誓要做一个好妈妈的。不打孩子、不骂孩子、不粗暴地呵斥她们。决不让我受到的任何一样伤害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但生活不是剧本。
照料孩子、照顾家人以及工作、写作和人近中年的危机意识。一个妈妈只有24小时。妈妈不是神仙。她要睡觉,疲惫时会暴躁,工作失败时会沮丧,身体会痛苦,情绪会低落。一个妈妈只是一个肉体凡胎。
我可怜的暴龙妈妈在那个年代,只有56天产假。一周只休息一天,那一天还要政治学习,上下班迟到一分钟都会被扣钱。上着班的她要养育两个孩子。她没有钱请保姆,虽有姥姥帮带孩子,姥姥则是她脾气暴躁动不动呵斥她的母亲。她面对着事业的挫折,面对着婚姻的各种冲突危机,我年轻的父亲事业风云直上,而同样学历、能力超群的她只能蹭蹬在小职员的位置,被两个孩子牵着鼻子团团转。
一旦我们弄灭了煤球炉,自然会遭致一顿毒打和毒骂。因为煮一顿饭,燃煤球炉就要10几分钟,而单位规定的午休时间,不过是一个半小时。所以走在路上,她会把看见的小木片都捡拾起来带回家,用作引燃的材料。孩子尿床、弄脏衣服了对她就意味着又一轮无穷尽的家务,冰天雪地时她也得下河边去捞洗,南方的冬天,水刺骨寒冷,冷得骨头发疼,你决不想把手在里面多放一秒,主妇却要在里面浸洗全家的衣服、被褥——逢上天阴,衣服被单,怎么也干不了,狭小的陋室里,晾也无处可晾。
妈妈在我这个年纪,一个曾经充满梦想激情的女人,生活变成了两个拖着鼻涕哭闹不休的孩子,一大堆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睡眠永远不足,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牙缝里每一分钱都抠下来持家,她怎么可能永远挂着圣母般的温柔微笑?早晨上班马上就要迟到,而迟到就意味着扣奖金扣工资挨批评写检查,她怎么可能蹲下来给哭闹着不肯吃早饭孩子一口一口喂饭?一个童年一直在暴躁的母亲手下忍气吞声的孩子,青春期在严苛的军营度过,经历了十年文革,周围充斥着暴力、辱骂、猜忌和冷漠的社会里,一个资源极度匮乏,随时都会挨饿的时代里,我的母亲,怎么可能不进化为一头暴躁的霸王龙?丛林的母狼对小狼没有温柔可言,对于犯规的小狼,连撕带咬、叼起脖子就甩地上,狠狠地毒打一顿,因为,生存争分夺秒。
为一毛钱在菜场争得口角冒烟,那是因为为嗷嗷待哺的孩子多争回来一口菜都是好的。她们偷偷地把单位信纸拿回家,给孩子写字。她们在单位食堂里把肉食夹在一边,装在盒子里带回去,晚上给孩子补营养。路过菜场,被遗弃的蚌壳也不能忽视,她顾不上泥泞脏污,检起来带回家,敲碎了给鸡吃,让鸡多生蛋。生活这样粗糙,珍珠也被磨砺得失去光泽。
暴龙妈妈用巴掌呼过来,让我们好好吃饭,即便饭菜再不可口,也必须吃得盘光碗净。为了贴补家用,她在院子里养了几十只鸡,保证两个孩子每天能吃上两只鸡蛋,周末会将多余的鸡蛋拿到集市上去卖,和一大堆的贩夫走卒坦然地挤作一堆叫卖。冬天里,她托人买紧俏的驼毛,密密厚厚地缝在绒布里,把我们的小手,包得象熊掌,家制的棉鞋丑陋,里头却穿着两双袜子,一双棉袜,一双毛袜。我从没长过冻疮。虽然没有零食,我吃得又饱又足,我和哥哥的身高远超我的同龄人。我恨她在16岁还给我穿家制的衣服,让我丢脸,但是,16年,每一件衣服,从内到外,衬衫衬裤,毛衣毛裤,外衣罩裤,都是她一针一线制出来的……春去秋来,一个妈妈得在缝纫机前、毛线针底下,付出了多少心血?
暴龙妈妈自己读了很多书,人聪明,勤快,写一笔飘逸好字,口才好,文章也练达,但在单位中始终不受重用——本来也不是一个重用妇女干部的时代,她又不会逢迎拍马。还天真地去劝诫领导的小蜜:你这样做是违反社会主义道德观的!换在美国,也许她会是希拉里。但在中国……
在小镇的集市上,熟人的眼皮下,她叫卖自产的鸡蛋。邻居女眷们取笑她:“你还大学生呢,就落得干这个?”我蹲在她脚边,虽然幼小,也感觉到羞耻的压力。妈妈昂着头:“劳动最光荣!”——这辈子,她都在给我唱高调。但她也是少有一个按照理想主义的高调生活和践行人生的,我所见的唯一一个。以最终的退休级别,她和父亲都有不菲退休金,子女亦无负担,但已近七十的她,依然每天工作,早晨八点到店,晚上八点回家。我笑谓她大有弘一法师之风度:“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她瞪我一眼:“不做事怎么行?在家等死么?”饮食依然极简,在庭院内外,栽种了蔬菜:青菜、香菜、胡萝卜、油菜、红薯、青蒜、香葱,每日菜蔬,自给自足。每个月开销不过数百,举手捐赠,却极慷慨。人越老,越清瘦,老花镜下一张清癯而严厉的脸。她是无神论的共产党员,不信基督,我十分遗憾地告诉她:“您这作派,您这思想,实在是和很多基督教的清教徒非常相像!”——近年来好多家庭开始自种菜蔬了,在报纸上看到,她嗤之以鼻地一笑:“早说了,我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
试着给她说:“我们出钱,请你去周游列国?老了也开开眼界?”她自负地一昂头:“我坐在家中,眼观天地,心游八极,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不过就这样那样罢了,能有什么新鲜?”
我告诉她,这句话和圣经里一句话很象:“日头底下无新事。”她鼻孔里又嗤了一声——那还用说?老太太我的智慧是你受用不尽的!
她把我塑造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也许是从臭气熏天的鸡窝里掏鸡蛋开始。也许是在集市上卖鸡蛋,昂着头冷笑的那一刻开始的。世俗的太多东西,在她那里被蔑视。所有的行动,在她那里,都是简洁的、直接的、明了的、实用的,所有的目的,也都是高尚的、纯粹的、和光明的。
她从来都不是完美妈妈,完美妈妈也只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她,就是妈妈。我也从来不是完美孩子,但若干年后,不完美在岁月中,慢慢长成了独特的印痕,成为生命特别的馈赠。
随着年纪深长,生命中的浮华,与青春一起次第凋去。如一个剑客练剑到了末期,去芜存菁之际,越来越觉得生活中很多事物的不重要。吃什么,也都那么回事,穿什么,也差不了多少。我越来越象我曾经激烈反抗过的她。有一段时间,一件西服我穿了五家电视台,录了三十档节目后,编导提醒我,你好歹也换换形象?难道你就这一件出镜西服么?我说:“若论服装,你们可以随时找一万个比我会穿的坐在这里——但显然你们不是需要这个,观众也不是需要这个。差不多就可以了。”
——暴龙妈妈当年劈头怒喝:“穿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什么!”
三十年的菩提子,三十年后终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