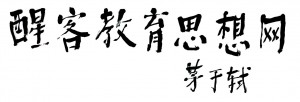原文作者 | nytimes 译者 | sibyl玥 发表时间 | 2014-05-26

学生们鄙视SAT不仅是因为它带来的强烈焦虑感,它是阻碍他们进入自己梦想中的大学的最大障碍,还因为他们不知道能从这项考试中得到什么。他们认为这项考试玩弄了一些巧妙的花招,提出的问题在高中课程中极其罕见。由于每做错一道选择题会倒扣1/4分,因此,学生们需要花时间去分析以决定要回答哪道题和弃答哪道题。
随着中国高考改革,英语将不再是高考的必考科目,而语文和数学的份量将加重。这样的改革究竟是好是坏?研究美国高考改革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
2012年7月,在大卫·科尔曼(David Coleman)正式就任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主席的几个月前,他邀请当时的麻省理工学院写作项目部主任莱斯·佩雷尔曼(Les Perelman)到曼哈顿下城区与他会面。美国大学理事会的众多工作包括参与研究、制定教育政策及编写课程,而其中最被公众认知的可能就是监管学习能力倾向测验(Scholastic Aptitude Test,以下简称SAT)了。佩雷尔曼是该考试最苛刻也最无情的批评者之一。2005年,美国大学理事会在SAT考试中增加了写作(总分值也从1600分上升为2400 分)。自此以后,佩雷尔曼一直着重研究他所认为的写作命题及评分的内在荒谬性。他最早的研究发现表明:与其他任何因素相比,作文字数与作文成绩的关系更为密切。最近,佩雷尔曼辅导了16名因写作成绩欠佳而重考的学生。他告诉他们细节重要而事实准确性并不重要。他说,“你可以告诉他们1812年美英战争始于1945年”。他鼓励他们使用少量生僻花哨的单词,如“plethora(冗余)”或“myriad(繁多)”。同时,他还鼓励他们使用两到三个预先准备好的名人名言(如: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无论这与问题是否有关。他说,重考后有15名学生的作文分数高于90%的考生。
当科尔曼被任命为大学理事会下一任主席时,他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有关佩雷尔曼研究的文章,因此决定跟他联系。上个月我去到位于林肯中心附近的大学理事会总部,在他的办公室里与他会面,他说道:“有人猛烈抨击SAT,那又怎样?他们获得了媒体的关注,那都没什么意思。但是,佩雷尔曼为我关心的事业奉献了一生。他教学生写作,并审视这种旨在赞美写作的方法。”科尔曼的话音逐渐减弱。“我想更加深入地研究他的观点,”他最后说道,“而非只是读读与他的观点有关的新闻访谈。”
在他们交谈的两个小时中,佩雷尔曼告诉科尔曼他并不反对写作测试本身。他认为这项工作如果做好了,也不失为一个好想法。但是,他问道:“在大学或在生活中,何时会有人要求你就你从没想过的东西写篇文章?我从未从老板那收到过这样的邮件:‘失败是否是成功的必要因素?25分钟后回复我?’但SAT就是那样做的。”佩雷尔曼谈到,辅导教师通常会教他们的学生去撰写并记忆一篇万能作文。这种作文包含获得高分的必要因素——“一个个人轶事或一些历史典故;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似乎是一个特别受欢迎的历史人物。”在考试当天,他们照搬所记住的东西,再针对问题将答案稍加变化。可是,没人真正学到任何写作知识。
科尔曼告诉我,佩雷尔曼对他们富有成效的谈话感到惊讶,但他根本不认为这次谈话会有多少成果。大学理事会是一个大型的非盈利组织,每年有数亿万美元收入(部分来源于它每年针对高中生举行的近300万场SAT考试)。尽管在过去它一直受到外界的强烈批评,但佩雷尔曼估计它从未有过实质性的改变。当时他认为:“大卫·科尔曼的想法是对的,他其实是信任教育的。” 但是佩雷尔曼还说,尝试改变大学理事会的经营方式,“就像试图使泰坦尼克号转向一样。”科尔曼的机构是出了名的行动缓慢、戒备心强,无论谁掌舵,这样的一个机构也不会改变航向。
到2012年10月科尔曼就职时,科尔曼不仅了解了佩雷尔曼的观点,而且也熟悉了更多来自大学理事会支持者的投诉,其中包括教师、学生、家长、大学校长、大学招生人员、高校辅导员。他们对这项考试不满,且均有正当的理由。
学生们鄙视SAT不仅是因为它带来的强烈焦虑感(它是阻碍他们进入自己梦想中的大学的最大障碍),还因为他们不知道能从这项考试中得到什么。他们认为这项考试玩弄了一些巧妙的花招,提出的问题在高中课程中极其罕见。由于每做错一道选择题会倒扣1/4分,因此,学生们需要花时间去分析以决定要回答哪道题和弃答哪道题。老师们也认为这项考试不是按他们的授课内容出题的。然而,国家教育部门会公布许多高校的SAT平均分,这意味着老师往往会成为学生考试成绩不佳的指责对象。
对这项考试更严重的指控是:因为富裕家庭的家长能承担昂贵的考前辅导班及辅导教师,所以它使富裕家庭的学生具有优势。几年前,莲花软件公司(Lotus Software)创始人米切尔·卡普尔(Mitch Kapor)在《旧金山纪事报》(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上与人合写了一个专栏。被上述不公激怒的他建议大学应该强制要求学生和家长公开“已购的所有形式的辅助”,以建立公平竞争机制。
SAT始于1926年,那时人们将其提倡为一种创建无阶级的杰弗逊式英才教育制度的手段。这项旨在评估先天智力的考试最初改编自一战军队智力测试。在20 世纪30年代,它被十几个重点大学用作奖学金评选方法。那时人们认为学生无法为先天智力测试做有效准备。但是,早在1938年,斯坦利·卡兰普 (Stanley Kaplan)便开始提供培训课,承诺提高分数。现今,无数小规模的专业辅导公司(且不说昂贵的私人教师)也加入卡兰普公司及其主要竞争对手普林斯顿评论(Princeton Review)的行列。这个年营业额达45亿美元的产业大大迎合了那些忧心忡忡的美国富人们的需求。这些富人们认为这项测试有对策可循,而他们的孩子需要的则是花钱学习对策。
美国大学理事会主席大卫·科尔曼在其任职期间对SAT考试进行了全面改革,使其能更好地体现学生在校期间应该学习的知识。照片由布赖恩·芬克(Brian Finke)为《纽约时报》提供
科尔曼与那些对大学理事会失望的支持者们举办了一次“倾听活动”。他当时认为,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机构,大学理事会必须承认它有很多不足之处。“不公平的考前辅导是一个问题,”他说,“考试范围不明确以及评分复杂亦是一个问题。我了解SAT背后的一些科学理念,而且我也欣赏其中大部分的道理。但是,由于那些随之发展起来的事物将这项考试由鼓励英才教育的工具变成了在美国教育中巩固特权的手段并对一切造成了威胁,我觉得某些改变是必须的。”
很明显,科尔曼说,无论家长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如何,他们都不会感到满意。富裕家庭学生的成绩并不是“干净”的,因为他们的分数是用钱“买”来的。中产阶级的学生则抗议不公,因为他们无法得到,或者需超额开支才可能得到“良好的考前辅导”;而那些贫困生,通常是少数民族学生,则完全被考前辅导拒之门外。瑞克·布里格斯(Derek Briggs)是位于博尔德的科罗拉多大学分校的研究和评估方法论项目主管。他在2009年的一篇论文中强调,除1000美元以上的课程费以及私人教师费以外,还有另一种考前辅导成本,他称之为机会成本,即学生花费大量时间一味追求考试过关,结果无暇顾及家庭作业和课外活动,而这些活动实际上是学生在大学成功的必要准备。
除了这些教育(及道德的)困局外,科尔曼还必须明白,作为一个企业,大学理事会却让SAT的可信度受到质疑,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数年前,几个小型的文科大学取消SAT并将相应的A.C.T.2(美国大学入学考试)作为入学标准。后来,由于对2005年SAT改革甚微感到失望,且受2008年全国大学招生咨询协会(Nacac)发布的报告所鼓动,越来越多的高等学府开始纷纷效仿。该报告的作者引用了加利福利亚大学的一项研究,将SAT描述为“不能准确预测学生表现”,并且质疑大学倾向于将SAT作为“最重要的入学方法之一”的做法。(许多撤销考试要求的学校,至少在第一年,出现了入学申请人数激增的现象。)
大约在报告公布之时,在维克森林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瑟夫·A·索尔斯出版了《特权的力量》一书,解释了标准化测试怎样推动了耶鲁大学的歧视性招生政策之后,威客森林大学就成为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出的全美前三十所大学里第一个提出选择性考试招生政策的大学。维克森林大学的后续研究表明,在学校停止将标准测试的分数作为考核因素后,入学新生的的高中平均绩点增加了。2012届新生中有79%的学生在其高中班级里排名为前10%。在实行选择性考试之前,此数目只比60%多一点。此外,学生的构成更加多样化。索尔斯编写了一本书,其中有一部分探讨了SAT在佐治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及维克森林大学的低预测准确度,他说,“考试成绩在很大程度上与家庭收入有关,但与高中成绩无关。”他接着说:“此外,我们的社会、种族和生活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化,这在校园里得到了体现。在我们采取选择性考试招生政策之前,维克森林大学的学生构成就像J.Crew3的产品目录一样单一。”
上个月贝茨学院招生办前主任威廉·C·希斯(William C. Hiss)和前副主任瓦莱丽·W·弗兰克斯(Valerie W. Franks)发布的研究报告支持维克森林大学的经验。他们评估了33所不要求SAT或A.C.T.分数的高等学校,发现参与测试与未参与测试的学生之间的大学平均成绩与毕业率无明显差异。特别是, 他们还发现高中成绩优异的学生在大学里的表现也不错,即使他们的SAT分数不高。而高中成绩较差的学生就算SAT分数优异,在大学里的表现仍较差。未参与SAT的学生往往是少数民族学生、女性、佩尔助学金4获得者或家庭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
尽管有更多的院校决定退出标准化考试,但全国大学咨询会的大卫·霍金斯(David Hawkins)认为,预计仍有80%的四年制大学要求SAT或A.C.T.分数。招生办负责人们也报告说已习惯于通过测试筛选数目惊人的申请者,感觉难以将其割舍。著名作家、康奈尔大学教授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对《前线》记者说,当他在耶鲁大学审阅入学申请时,他难以忽视分数。“我意识到当我在阅读申请书时,随着夜晚渐深,阅读的申请书越来越多,我会越来越看重SAT分数,”他说,“这比阅读长篇的论文及老师的推荐信更简单。这是人的本性。”除了筛选申请人的压力,全国大学咨询会的报告还提到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因采用SAT及A.C.T.分数来给大学排名而导致的问题,表明分数“不能有效评估重要的品质”。此外,它还批评证券评级公司采用SAT及A.C.T.来协助评定学校财务状况,认为这“对招生办施加了不必要的压力以追求越来越高的测试分数。”
科尔曼说,许多与他交谈过的招生办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依赖这类考试,至少是依赖这项考试让他们心里不舒服。但是,怎样的考试会让所有人认为公平且愿意接受,他们并没有一致意见。
科尔曼一直沉迷于解决难题。1994年,在科尔曼获得耶鲁大学哲学学士学位,牛津大学英语文学学士学位(同时他是牛津大学罗德奖学金5的获得者)以及剑桥大学古代哲学硕士学位( “即使拥有三个学位也无法获得就业机会”)之后,科尔曼打算回纽约,去一所公立学校当老师。但当他发现无法找到一份高中英语老师的工作后,他成为了麦肯锡咨询公司(McKinsey & Company)的一名咨询顾问。在这里的五年中,他越来越沉迷于以证据为基础的来解决问题。在那段期间,他曾为想要提高教学质量的学区提供无偿服务。1999 年,他离开了麦肯锡咨询公司,并帮助创建了成长网络公司(Grow Network)。该公司主要致力于帮助学生及家长(包括非英语家庭)应对越来越受标准化测试影响的教育制度。他与教育者和学生们进行交流,沉浸于对标准化测试的研究之中,这让他确信必须改变那些考试要测评的能力标准,因为那使得考试过于庞大和模糊,而且人们在生产教科书时也同样毫无目的。
科尔曼说:“当测评范围过大时,用于测评那些标准的测试必定是肤浅的。”他指出有研究表明现在有更多的大学新生并未做好准备,于是被迫参加“从未摆脱过的补习课程。”以数学为例,如果你研究成绩最好的国家的数据,你会发现它们的学习方法强调“范围窄,研究深”。相反地,他发现美国的课程则是“一英里宽,一英寸深” 。
2008年,科尔曼协助创立了一个名为“学生成就伙伴”(Student Achievement Partners)的非盈利组织。该组织坚持在决定教育方针时“依据行事”。在该组织期间,科尔曼对塑造《共同核心6》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共同核心》是一套完整的学术标准,已陆续在40多个州实行。虽然这个标准不乏批判者——许多家长和教育者认为它让一种有问题的“应试教育”思想在学校和教师中根深蒂固——但是科尔曼认为,它不仅是抵御美国公共教育的水准下降的堡垒,还是是一次罕见的两党合作。在去年五月波士顿召开的战略数据项目报告会上,他要观众说出一个“共和党和民主党曾同心协力有所成就的重要国内政策领域”。他说,《共同核心》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想法,“在一切想法似乎都止步不前时,它却风靡全国。”
当科尔曼就读于曼哈顿史帝文森高中(Stuyvesant High School)时,他曾是辩论冠军队的一员。显而易见的是,与人交谈时他总是迫切地想要用证据制服对方,并对愚人极不耐烦。(他说辩论是为数不多的“使人极度好辩并助人进步”的活动之一。) 2011年4月,在纽约州教育部门组织的一次推广《共同核心》的会议中,他得罪了在场所有的教师和行政人员。在表达对高中作文注重个人叙述的不满时,他谈到成人生活的现实:“别人真[脏话]不会在意你的想法或感受。”当那时的视频在网上疯传之后,他道歉并解释说,他当时是在提倡一种在大学及职业生涯中无疑有用的技巧,即基于证据的分析型作文。但他的言论还是加深了一些人对他的坏印象,他们认为他麻木不仁且激进极端,是那种自以为是的万事通。
2012年10月,在迈阿密举行的美国大学理事会年度会议上,他间接引用了这则逸事,同时还提到自己习惯使用直率多变的语言。他还开玩笑说人群中有“惊慌失措的”理事会成员。
参与制定《共同核心》给他带来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即美国的教育需要多些专注少些肤浅,且它应该能够通过反映课堂教学的考试来评测新定义标准的成效。 这正是大学理事会主持的大学预修课程7(Advanced Placement)项目的运作程序(在福特汉姆研究所(Fordham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中,参与调查的80%的教师表示,大学预修课程考试能较好地反映他们的工作情况以及学生的学习情况)。这也是全国大学招生咨询协会2008年报告中的一项主要建议,即大学录取考试应重新设计为类似于美国大学预修课程考试的成果式测试。这将会给学生们传达一种信息——学习他们的高中课程以及不参加以应试技能为主的课外备考课程是在大学录取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及适应严格的大学课程的方法。
对于科尔曼来说,问题在于如何让一项考试准确评测学生成绩及大学学习适应能力,且逐步向原先期望达到的精英化目标发展,而非妨碍目标发展。
一年多前,科尔曼与一批大学理事会工作人员及顾问开始尝试进行这项工作。大学理事会的主要评估员辛蒂·施迈瑟(Cyndie Schmeiser)告诉我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这项考试要测评的能力。从2012年底起直到2013年春季,她和她的团队与学生、教师、家长、辅导员、招生人员及高校辅导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要求各类人员详细地告知他们对测试的期望。他们首先得出的结论为:一个测试应该反映最优秀的老师传授的最重要的技能。施迈瑟解释到,例如,一个好的导师教授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时,应鼓励讨论,包括分析文章及找出有力的(事实或修辞性)论据。“我们不想老师只会在课堂上询问:‘这篇演讲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表的?’”施迈瑟这样说道。
随后辛迪·施迈瑟的团队着手设计了一些考试题目以投入到这项更有意义的事业中。施迈瑟曾有言,过去SAT的出题非常注重实用性,即对大多数学生而言,这些题目的难易程度是否合适;针对来自不同民族、种族和宗教的考生,这些题目是否没有任何歧视?考试目的是将考生的“差异最大化”,即要找到好学生能答对但差学生不能答对的问题。科尔曼说,达成此目标的一个简单办法是考查一些晦涩词汇,这也是SAT著名(或臭名昭著)的手法。他还说道,考试结果在数据上与预测极为吻合——只有少部分学生知道这些词汇,而大多数学生则一无所知——但是这一结果并不能充分反映科尔曼所信奉的教育意义。美国大学理事会在重新设计考试时改变了考试重点,优先考虑考试内容,测试的每个问题则要参照一系列能反映出学生将在大学和工作中遇到的阅读和数学问题。去年年初,施迈瑟和其他工作者一起花了大量时间来观察学生在回答大约20一组的问题时的表现,并在考后与这些学生一起讨论这些问题。施迈瑟在谈到修订版考试时说,“新版对学生正确率的预测准确度还是和旧版一样,但是在新考试中,我们能更好地控制考查的内容和技能。”
上个月,我与科尔曼在他办公室会面,讨论SAT的改革。谈到令他激动的想法时,他会时不时地从椅子上跳起来。有一次他跳起来在白板的中间从上到下画了一条分界线(他非常喜欢使用白板),然后在线的一侧写到“以证据为基础的阅读和写作”,另一侧写到“数学”。他正在白板上展示过去数月的反思与测试所得到的结果。
从2016年春季开始,学生将参加新的SAT——延用旧考试系统中长达3小时满分为1600分的考试,另外附加一篇单独计分的可选作文。科尔曼说,以证据为基础的阅读和写作将会取代目前的相应部分。新的阅读和写作将以科学文章,历史文献和文学摘录为素材,因为研究表明,这些材料是受过教育的美国人理应熟知并深刻理解的。科尔曼曾言,“在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利法案》和《联邦论》都引发了关于自由、公平和人格尊严的重大讨论”,——因此,每一次SAT都将从建国文件或者从这类文件激发的“伟大的全球性讨论”的文章中节选一部分,比如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8》(Gettysburg Address)。
科尔曼给我举了一个相关的简单例子。学生会读到一段摘自德克萨斯代表芭芭拉·乔丹(Barbara Jordan)于1974年的讲演节录 。在这段节录中,芭芭拉说对尼克松的弹劾将把人民划分成两派。这时学生要回答的问题是,“乔丹话中的‘派’是何含义?”并且问题后有几个选项供选择。此类词汇问题会取代目前SAT中深奥难懂的问题。这种设计思路是,考试应该注重学生可能会遇到的多义词,比如“合成”(synthesis)。这类词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有很多意思。考试不应该鼓励学生死记硬背,相反应当提倡在高中阶段进行广泛阅读。
关于芭芭拉·乔丹的这道题还有后续题目:“你如何知道你选的答案是正确的?”要回答这道题,学生必须在文中划出能证明自己选项的文字。(到2016 年,SAT将有机考版。到那时学生可以在电脑上检索并标出相关原文。)考试还要求学生审查文本和数据,包括找到并改正两者的不一致。
科尔曼说,“任何时候当一个问题在大学或工作中有其重要性时,仅仅给出一个答案是远远不够的。至关重要的是提供证据来证明你的答案(这样别人就能了解学生的真实水平)。这项改革对学生的考前准备来说意义重大。只重视技巧和排除选项法再也行不通了。我们关注的不是学生对选项的选择,而是他们对其选项合理性的证明。”
要实现这点,写作部分的题目也会修改。如此一来,所有的题目都会遵循一个思路:“读文章并思考作者是怎样把事实或者实例当成证据来使用的,如何展开思路以及怎样将论点和论据结合起来,以及如何用极具风格或说服力的内容增强所述观点的力度,然后写一篇作文解释作者是怎样进行论证来说服读者的”。考试选取的段落会不停变化,但分析和论证能力将会一直作为考察重点。科尔曼说,“学生会被要求做一些我们每天在工作和大学里做的事情:分析材料,理解观点并加强论据。”
数学部分也会以研究结果为基础考察“许多大学课程(和行业)必备的数学知识”。科尔曼承认,有人可能会以为由复杂题变成基础能力题会使考题简单化,但是他坚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解释道,数学部分会重视三个方面:一是问题解决和数据分析,包括比例、百分比和其他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数学推理;二是核心的代数问题,考查学生处理线性方程(“广泛运用于许多科研领域的有力工具”)的能力;三是人们所说的“前往高等数学的通行证”,这方面将着重考查学生是否熟悉复杂方程及其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
去年六月,在哈佛夏季学院(Harvard Summer Institute)的多天研讨会上,科尔曼就高校招生和专业咨询人员问题发表了讲话。发言前,他与威廉·菲茨西蒙斯(William Fitzsimmons)进行了会面。威廉·菲茨西蒙斯长期担任哈佛招生部和经济资助部主任,同时还是2008年美国大学招生咨询协会委员会报告的主要作者。为了给菲茨西蒙斯留下深刻印象,科尔曼带去了一份SAT改革大纲。
菲茨西蒙斯告诉我,他看了那份大纲后完全惊呆了。其中的考试设计似乎是对08年全国大学招生咨询协会委员会报告提出的最重要建议的直接回应。“与任何极为重大的改革一样,这项改革必将引发争议。”他补充道。然而他又继续说道:“在过去,有时考试会让人觉得它是在考察一些难以衡量的素质,诸如资质与能力,却丝毫不顾‘资质’和‘能力’究竟意味着什么。而现在的改革则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努力和成果都将得到相应的回报。这是我从事高等教育招生工作四十余年来见过的极其重大的进步之一。”

数据来源:美国大学理事会
然而,单纯改革考试内容并没能解决盘踞在科尔曼心头的所有问题。他仍为教育机会的各种不公感到困扰,并认为美国大学理事会应在缓解这些问题上发挥作用。一段时间以来,理事会已对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卡罗琳·霍克斯比(Caroline Hoxby)与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Harvard’s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公共政策与管理教授克里斯多佛·艾弗里(Christopher Avery,)的研究工作有所关注。他们一直以来致力研究贫困优秀生源与一流大学之间的低匹配情况,即家境贫寒的学生倾向于选择离家近、门槛低的大学,即使他们完全能够成功申请其他大学。霍克斯比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在2004年,当时她任教的哈佛大学高调宣称学校将录取一批经济困窘的优秀学生,并提出若其父母收入低于四万美元,将予以免除学费。然而尽管如此,优秀贫困生的入学人数仍然很少。当霍克斯比开始研究这一现象时,她推测仍有大量家境贫寒的优秀学生未被学校发现。于是,她和艾佛里开始与美国大学理事会和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机构合作,共同开发新方法,确定优秀贫困生人数及其所在地。通过综合各方数据(数据来源包括普查报告、美国国税局(I.R.S.)提供的各邮区收入数据、房产评估及其他来源),他们锁定了三万五千名优秀贫困生。这些学生的成绩名列全国前10%,而其家庭收入却处于全美高考家庭的倒数25%。
当他们继续了解这些学生的院校申请情况时,他们发现了一项足以令科尔曼震惊的数据:56%的学生并未申请任何一所名校。
研究者们推测造成这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在于通讯不畅:信息没能传达给需要的学生和家庭,即便有时能够传递,所传递的信息也不够清晰有效。霍克斯比与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萨拉·特纳(Sarah Turner)一起进行了一项实验以测试他们能否改变现有录取模式。2010至2012年,霍克斯比团队陆续向家境贫寒的优秀学生发送信息详尽、具有针对性的材料包裹,鼓励他们申请更多大学,并免除申请费用、提供奖学金资助信息。许多情况下,通过这些信息,优秀贫困生会发现自己能够获得更多一流大学抛出的橄榄枝:这些大学为了吸引他们,能向其提供更为丰厚的助学金。霍克斯比团队的这一做法不仅促使优秀贫困生申请更多高校,而且缩小了“同等水平但贫富悬殊的大学生之间的表现‘差异’”(据霍克斯比和特纳记述)。
科尔曼当选为美国大学理事会主席时,他简要了解了目前为止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辅助工作。他赞同这些有先见之明的人的做法,还决定“要将这一小范围实验逐步推广至全国。”他提倡通过更多的调查研究来搜寻理事会认可的“已做好大学入学准备”的贫寒学生(“已做好大学入学准备”即SAT得分为1550及以上,成绩排名位于全美高考考生前43%)。最终,理事会寄出了将近10万个材料包裹给那些表现优异、“已做好大学入学准备”的学生。这些包裹含有至少四封申请免除书,让学生能够直接申请参与该项目的2000多所大学。据科尔曼所言,这些院校必须同意大学理事会做出的财政决定,学生也能直接获得助学金或特殊学费减免,不用再重新申请资格。这些申请免除书就像一张入场券——“拿上你的入场券,出发吧!”科尔曼说道。——这些入场券不仅简化了申请过程,而且鼓励学生赶紧把握机会。关于该项目初步成效的研究直至下月才会公布,但其进展速度已然兑现了科尔曼关于加快该事务日程的承诺。
2013 年1月,在于佛罗里达举行的一次由美国大学理事会主办的会议上,科尔曼会见了富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Franklin & Marshall College)校长丹尼尔·波特费德(Daniel Porterfield)。波特费德因卓有成效地将家境清贫的优秀学子纳进他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的小型文科学院而引起全美关注。他对霍克斯比团队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问题并不在于缺乏优秀的贫困学生,而在于高校搜寻人才的力度不够。而富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之所以能在这方面取得成功,也主要由于他们致力于搜寻出生贫寒的优秀学子。现已是美国大学理事会董事成员的波特费德告诉我,他认为科尔曼别具一格地“将美国大学理事会用于造福社会,而反对理事会为其自身谋利”。同时,他还提到在他与科尔曼的首次交谈中,科尔曼承诺美国大学理事会将帮助富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发现既才华横溢又勤奋刻苦的优秀学生,而他也“很好地履行了这一承诺”。
科尔曼发现,这一干预的令人兴奋之处在于它以标准测试为手段,帮助学生进入那些原以为遥不可及而放弃申请的学校。这使得SAT由一个被普遍视作负担的考试(过去许多出生贫寒的学生干脆放弃参加考试)变成了一个机遇。科尔曼解释说,学生拿到考试结果时必定是全神贯注的,而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将他们手中的分数与他们可能的未来连接起来。“你何时从SAT中得到过什么?”科尔曼这样说道,想象着学生们打开成绩单并且把申请免除书握在手中时的反应。
在过去的一年半里,虽然科尔曼及其同事意图是好的,也实现了以事实为依据的观念,但是富裕地区好学校的学生与低收入地区的学生在教育经历方面仍存在差异。当科尔曼与其同事继续推进SAT改革时,永远也无法让所有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事实让他们感到苦恼:他们最想鼓励的考生们依然无法获得良好有效的考前指导。
他们开始考虑该如何向六至十二年级的老师(特别是执教于教学质量较差的学校中的老师)提供更为广泛的考试资源获取途径,以帮助学生备考。去年七月,在 去参加纽约北部一个员工退修会的公车上,科尔曼团队的两名资深成员辛蒂·施迈瑟(Cyndie Schmeiser)和杰夫·奥尔森(Jeff Olson)提出了一个想法:何不让美国大学理事会与可汗学院(Khan Academy,免费在线辅导网站,每月访问量达千万)合作,向任何需要SAT辅导的学生们提供免费辅导呢?学生登陆可汗学院网站后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为时数周或数月的各科练习,并密切关注自己的进步情况。如果他们需要帮助,他们可以观看上千个由网站创始人萨尔曼·可汗(Sal Khan)制作的轻松有趣的学习视频。可汗拥有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多个学位,并担任了该网站的各项指导。当文字和数据出现在电子黑板上时,他的声音便开始解释如何解答各种难题。
可汗低调建立该网站的初衷只是为了通过互联网来辅导他的小侄女。后来,当她的亲戚朋友也希望得到他的指导时,他就开始在YouTube上发布视频。随着网站发展,可汗解决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旧版SAT考试中的一些问题,他说现在他可能没有权限再使用这些资源了。

大卫·科尔曼正集中精力研究如何鼓励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入读一流大学。照片由布赖恩·芬克为《纽约时报》提供。
科尔曼和他的团队对可汗学院的工作已有所关注,且有意向与其合作,但是同时他们也很谨慎。科尔曼说:“当你想说‘好’的时候,又会想‘但够好吗’?”美国大学理事会此前从未进行过类似的合作,而且他担忧合作可能会给理事会的名声带来不好的影响。
纵观去年秋天,他的员工在可汗学院网站上花了很多时间。先创立一个透明化的考试形式,然后提供一个任何学生都能使用的免费网站——不是让学生学习投机取巧的方式,而是对考查的核心知识进行更好的基础练习和额外训练——这种创意吸引了科尔曼。
可汗将体育竞技中的现象作为他们行动的依据。在运动中,为了参加比赛,你需要一直练习。尽管比赛期间的风险很高,但却不会如SAT一样普遍让人感觉倍受折磨,也不会让人产生焦虑的副作用。他说,不同的是,运动对参赛者的要求都是透明的,比赛规则是清晰不变的。而SAT 的规则并不清楚。科尔曼说:“焦虑多半源于对‘比赛当天’的不确定性的恐惧。这不见得公平。高风险不应该被加诸于一些之前不重要现在突然很重要的事情上。风险必然会产生是因为之前所作的努力很重要,而在考场上发挥出应有的实力更重要。”
体育竞技所需的长期专项训练方式与可汗学院采取的方法不谋而合。从理论上看,无论如何这种合作都是行得通的。
今年一月,科尔曼会见了民权与人权领导会议主席及执行总监韦德·亨德森(Wade Henderson )。亨德森与他讨论了弱势群体对SAT产生的仇视心理。长期以来这个考试并没能为他们提供一个通向更好未来的跳板,反而成为了勤奋学生的阻碍,因为他们无法获得富裕学生能够获取的资源。科尔曼也承认 “SAT考试极大地反映了收入不均的现象”。他还说,亨德森还担心SAT低分不利于找工作。整整一个小时的谈话让科尔曼感触颇深,他决定在考试改革中增加一个因素。发送至各个机构的考试信息都将用红笔注明“谨慎使用”:“本信息只能与其他相关信息共同使用,以便作出对学生负责的决定。“
与亨德森的谈话过去几周之后,科尔曼飞往硅谷去和萨 尔·可汗谈论合作事宜。他们讨论的并非金融条款,只是在原则上同意两人将携手合作。(美国大学理事会并不资助可汗学院。)他们讨论了一种仍处于设想阶段的考试辅导:学生们可以登录到一个个人面板上,表示自己想要为SAT做准备,然后完成一系列的预备问题,展示自己的初始技能水平并找出知识上的不足。可汗说他可以预见一种能够评估达到某一标准所需花费的时间的方法。他说:“就像这样:‘好的,如果你每天投入半个小时的话,我们认为你能够在一个月之内达到这一水平,在两个月之内达到那一水平。’”他还认为,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只要他们能保证将按照规定投入精力,那这一网站一定能预测他们的理想分数。
科尔曼告诉可汗,大学理事会将通过一些组织(比如男孩女孩俱乐部和大哥大姐俱乐部)投资一项拓展项目,以便让尽可能多的学生们从中受益,尤其是那些目前还不是这一网站的主要使用者的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们。科尔曼还让可汗参与制定实际的考试试题,所以可汗正为即将参与旧式考试的学生们制作材料。(他说这月初就会面世。)科尔曼对我说,当可汗告诉他他们正根据网站上那些对学生最为有益的东西来不断改进材料时,他更加坚定了这次合作的信心。可汗相信通过适当指导,任何学生都能达到更高的技能水平,这一信念尤其鼓舞了科尔曼。可汗曾问科尔曼是否知道五个世纪以前,人们抱有一种相类似的误解。科尔曼解释道:“他说,‘大卫啊,你知不知道在过去人们相信大部分人是没有阅读能力的?’”
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科尔曼好几次都提到了一些备考培训班,称它们是以家长和孩子的焦虑为食的“猎食者”,对学习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虽然考前辅导的效果还无定论,但许多研究表明它平均只能提高30%的成绩。)谈论到新考试及他和可汗学院的合作时,科尔曼说:“这对他们来说将是不幸的一天。”
然而,科尔曼也承认,改革后的SAT并不能止住所有的抱怨声,他也不期待全世界人民都为他们额手称庆。你可以想象将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标准化考试能否对所有群体都是公平的,以及大学理事会最终修订出的新型考试是否会像旧考试那样总被一些人通过一些方式钻空子。
面对这些担忧,科尔曼回应说这一新型透明的考试将与高中的教学内容挂钩,并且将有证可循。露西·卡尔金斯说:“大卫·科尔曼虽是教育工作者,但并未受过专业培训。”她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读写计划的创办主任,还是《通往〈共同核心〉之路》(Pathways to the Common Core)的作者。虽然她是《共同核心》的忠实拥护者,但她认为科尔曼过于固执己见,坚持用他自己的特殊方法来执行《共同核心》的标准。她引用了科尔曼曾参与制作的一个讲解《解葛底斯堡演说》的“模范课视频”,说在这个视频里,他让学生们花几节课的时间“剖析每一段中每一个词的意思。”她觉得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一方法是有效的。
卡尔金斯认为,一份重新设计的SAT可能会使美国教育课程和评估的走向过多地掌控在一个人的手中。“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让大卫·科尔曼掌控整个K-12教育11课程体系?”
威廉·菲茨西蒙斯是全国大学咨询会主席兼哈佛大学招生主任,他个人对科尔曼的改革速度印象深刻。菲茨西蒙斯告诉我:“在教育界,这算是闪电般的速度了。”人们对其不等效果如何就推进改革的激进做法表示担优,但是科尔曼对此并不接受。他说他相信,如果一个人像他一样费尽心血收集了论据来支持自己,那他就能以此来抵御别人的狂妄自大和错误想法。他说实际上,他的决定并没有那么胆大妄为,它们都有可靠的研究支持。当然,这正是他和露西·卡尔金斯这类批评者们有所分歧的地方,但是就像所有雄辩家一样,科尔曼似乎知道何时应该运用真凭实据,何时应该用具有说服力的华丽辞藻来将证据包装。他总是解释清楚,岌岌可危的并不是一个考试的公平性和实用性,而是我们国家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公平机会的能力,而这实际上是这个国家的灵魂。他是否找到了解决之道?我们还得拭目以待。
[ 原题 | 揭秘美国高考改革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