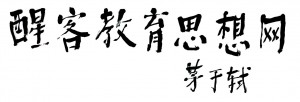演讲者|周作宇 时间 | 2011-05-13 地点 | 中山大学 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2011年会现场
我今天下午要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惯习与教育改革的本质》。关于这个题目,我想提一个问题,阐述四个观点。
教育改革搞了很多年,回顾过去30年或者更长时间,中国教育实践尤其是教育改革的实践,我们需要追问一个问题,指导改革实践背后的教育哲学是什么?从改革也好、实践也好,不是这样的哲学在指导,就是那样的哲学在指导,我们要问,指导中国教育改革的教育哲学是什么?这是我和大家交流之前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共同的思考和讨论。
下面阐述四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教育学有三种形态,不是一种形态。在教育实践的过程当中,围绕教育实践展开的反思和理论结构有三种教育学起作用或者可能起作用。第一本教育学是官方教育学,第二本教育学是学院教育学,第三本教育学是民间教育学。也就是说,教育学是三种形态共生的一个系统。
我们经历了许多发生在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一些争论,也目睹过学者和一线教师、校长的争论,普遍有一个发现,就是大家分别在不同的场域、不同的区隔用自己所熟悉的一套话语体系在阐述自己的观点。
官方教育学说要回答的问题是教育实践具体问题的一些行动方案,要拿出方案来。在上午的争论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切实感觉到官方教育学它所主张的、所坚持的一定是要针对现实当中真实的问题、具体的问题,就先有的条件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也就是官方教育学必须要表明立场,必须要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能够求得一个平衡。所以,官方教育学无不打着政治的色彩,这是第一本教育学。
第二本教育学,就是学院派的教育学。学院派的教育学也是旨在回应问题、解决问题,但是学院派的教育学旨在建立通过批判、建构理论、建构概念体系,由理论和概念体系再反射到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教育学的学制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院派教育学创制的一个最大的主体。
第三本教育学,就是民间的教育学。民间的教育学就是具体支配着人们日常行为、支配着人们日常教育行为的教育学。我们可能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确实客观存在,并且主导性地发挥作用。
为什么这么说?我举几个类别。首先是官方教育学和民间教育学的差别。去年寒假放假之初,一个行政部门负责人下午刚刚签署一个文件,禁止各个学校、各个学区给学生补课。签署之后,很快拿起电话问他在学校的朋友,“今年寒假哪个地方有什么好班?”——非常典型的官方教育学和民间教育学的差别。
在学院教育学和民间教育学之间也有类似的困境或者尴尬,我们的教育学人在课堂上讲的学院教育学可能是一种形态,但是回到自己的私人空间、自己的私域,和自己的太太、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的先生对话的时候,则使用民间教育学。比如和孩子的对话,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完成作业,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去弹钢琴等等。如果按照学院的教学,尊重学生的自由,尊重学生的选择等等,它是一种理念,但是行动当中不行,这个尴尬的案例也出现在我本人身上。
事实上,在整个教育活动当中,什么在起作用?根本来说,我以为就是民间教育学在起作用。民间教育学就是和各人的教育行为牢牢地绑在一起,深入骨髓的一种指导教育行动的文化。
第二个观点,教育的本质是秩序和惯习的改变。由于民间教育学的客观存在,在教育改革过程当中,必须清晰地意识到支配人们的教育行为究竟是哪本教育学在起作用。如果考虑到支配教育行为民间教育学在起作用,那么在教育改革具体规划、执行、落实、评价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把惯习纳入到教育改革的范畴当中,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要把教育改革的本质就界定在教育惯习的改变。
关于这个观点,其实教育改革专家麦克佛伦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讲任何一项教育改革,如果没有一线教师的参与,这种改革最终将流于失败。为什么会这样?教育最终要发生在课堂,教育最终要发生在生活的场景当中。而课堂也好、场景也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惯习在流动,而不仅仅或不完全是我们在教科书所讲的教育学在起作用。
当然,教育改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秩序的改变。我们所提到的教育体制的变革、教育制度的变革、教育结构的变化,所有这些在哲学的层面上我以为就是一种秩序的改变。
秩序的改变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如果比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种不同体制的差异,就会发现后者和前者所发生的变化,就是一个秩序的变化。这个秩序很大程度上就是根据什么来安排人们的日常生活。什么是支配人们行为的根本动力呢?基础来说,就在于人们长期形成的对日常经济活动的观察,原动力来自于人们的利益追求。制度的安排就是创造良好的环境,这种良好环境帮助人们实现他的利益。
从教育改革的角度来看,教育秩序的变化、教育体制的变化固然非常重要,所有这些秩序的变化,最后都要落到一个惯习的改变。
美国在1990年代末期的一个教育改革方案,曾经提出一个目标,在21世纪美国的数学和科学要实现全世界第一。今天上午我们听了上海张民选教授关于的比较,美国没有实现。美国没有实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秩序变了,但他的惯习还没有变。惯习的改变需要漫长的过程,因此改革的过程当中必须考虑时间的变量、历史的变量。时间的变量和历史的变量一定要纳入到教育改革的范畴当中。
第三个观点,在三本教育学支配下的教育改革,如何看待教育,教育的实质是什么?我认为教育的实质,或者用传统的话来说,教育的本质就是进入到另一个心灵的深处,通过自身行为的改变,来促进别人改变的活动。
为什么这么讲?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教育惯习是把教者和学者分开,教者和学者之间有一个生活空间的区隔,这样一种区隔长期以来是阻碍或者很大程度上限制教者能够俯下身来真正进入另外一个人的心灵世界,了解他的人治结构,了解他的情感世界,了解他的道德生活。如果进不去,很难真正体现教育的真谛——灵魂的上升。
第四个观点,考察我们的教育系数、考察我们的民间教育学,我认为我们存在着巨大的学习障碍和学习差距。这个学习差距反映在几个方面,第一,把学习器官简单地认为是大脑,但是我认为身体是重要的学习器官,所以要用身体来学习,用身体来思考,因为很多习俗恰恰就是埋藏在我们身体当中。第二,要超越正确的学习。我们现在很多学习就讲究正确的结果,而不考虑错误对一个学生发展的价值,也不考虑错误对整个教育政策发展的价值。所以我想,由教育正确结果的学习要走向从错误中学习的学习。第三,要强调反学习、续学习或相对学习。教育的习俗怎么才能改变呢?必须要遗忘,最近有一个词,有人翻译成续学习、有人翻译成反学习、有人翻译成相对学习,目的都是用全新的思想来接受外界的环境,来通过个人的行为改变外面的环境。
我的报告结束,谢谢大家!
现场问答
阎凤桥:周老师非常有启发性地讲了三种教育学,我想问一下,您怎么看待学院教育学和民间教育学的这种分离,有没有可能两者能够结合起来?
周作宇:谢谢凤桥的这个问题。事实上,民间教育学是可以转化的,学院教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民间教育学的提升。民间教育学的形态是和人的日常教育行为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日常教育行为是以无意识、潜意识、潜在的方式存在的,而学院教育学恰恰是让一些潜在的、无意识形成的一些信念、信仰、假设显性化,然后,通过将之进行理性的思考、理性的辩驳,上升到一个理论体系和概念体系的高度,所以民间教育学和学院教育学之间并不是绝对分裂的。民间教育学的学习方式是隐性的学习,学院派教育学的学习是显性的学习,隐性学习和显性学习是互补的,民间教育学最终要走向学院教育学,学院教育学需要从民间教育学当中汲取力量,所以这二者之间并不完全是截然对立和矛盾的。但是人们的日常行为选择往往受多种因素的约束,而学院教育学恰恰是简化了很多外部的约束条件,以模型的方式存在的,可以说是一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对冲和对撞,所以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孙绵涛:能不能把官方教育和民间教育学的文本说一说?
周作宇:官方教育学我以为主要体现在官方的政策文本当中,民间教育学就是实际执行过程当中反映在行为当中的教育学。比如说课程改革,2001年这个课程改革可以说是官方教育学糅合了学院教育学而形成的一个改革方案。在这个改革方案执行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现象。我曾经去过一些地区,了解到的情况是他们往往有两个版本的材料,一个版本是应付督导的,另外一个版本是准备考试的。教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如果按照官方教育学来说那就一体化了,就是一本材料。为什么在具体的学校操作过程当中还有使用两本的情况,我以为根本来说还是民间教育学在起作用,这就是官方教育学和民间教育学比较差异的一个个案。那我再解释一下,我说的三本教育学是比喻的说法,因为任何够得上“学”的,它一定有一个比较内在一致、逻辑一致或者历史一致的一个系统,所以我说的这三本教育学,如果写成文字,都是加了引号的教育学。
听众:是不是可以这样总结,教育改革最终要落到惯习的改革上面来,如果教育改革最终要落到惯习的改革上面来,是不是意味着以后的教育改革要开始注重微观个人的改革和潜意识的改革呢?
周作宇:你的观点也是对我的观点的进一步阐述,我今天主要是以惯习作为核心的概念,教育改革本质其实还有一个词,就是秩序,秩序和惯习是有差别的,秩序改变是在宏观层面调几个元素的关系就可以了,但是调了之后能不能起到最终的作用(则要看具体情况)?你比如说大学合并,当时大学合并就是一种治学的变化,变化以后能不能实现合并前的目的,就取决于大学里面的行政人员、教师、学生的变化,那就是一个惯习的变化。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我同意你刚才的一个延伸,教育改革最后要改变人的惯习,但是一定要把惯习放在秩序当中,或者换一句来说,把惯习放在场域当中,跟场域结合在一起。还有一个权力的概念,我这里就不再展开阐述了。
周作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