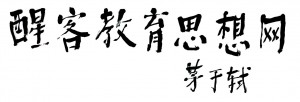作者 | 杨启亮 发表时间 | 2014–6–20 来源 | 教育学术月刊

讨论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之间的适切性,应该确认,适切不是个单向度的或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双向互动、渐进渐变的过程。应该考虑,适切不只是在课程与教学之间发生的,它们都有个与基础教育适切的问题,适切与基础教育的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教师和每一个学生都息息相关。在具体的课程与教学中讨论改革的适切性,主要是个文化选择、方法选择的问题。
我十年前曾经认为,在基础教育的课程与教学改革中,制定课程改革规划、制定新的课程标准、编写新的教材和教参,只是课程改革迈出的第一步,接下来的教学实践问题,必将有百倍的艰难。如今我们经历了并且还在继续经历着改革的艰难,也还在继续接受着实践的检验,在这样的情境下讨论适切性,与我们改革之初有什么区别?
我们起初会较多关注教学适切于课程、常态适切于改革、实践适切于理论,或者简单地把它们颠倒过来,关注课程适切于教学、改革适切于常态、理论适切于实践,如今我们应该承认,适切是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我们起初会较多在课程与教学之间讨论适切,如今“评价是改革的瓶颈”已成共识,我们应该觉悟到基础教育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人的终身教育的基础,也就能深入思考为何适切、为谁适切的问题。我们起初会较多关注与国际接轨的适切,如今我们应该体验到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独特的,任何学科的课程都是具体的,也就应该思考,改革如何尊重自己的文化?如何针对具体的课程、实在的教学。
简单的理论遭遇到复杂的实践,复杂的实践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疑问:我们的改革是否缺少了些基础性的共识?譬如何谓适切、为何适切、为谁适切、如何适切等等。
适切:一个双向互动的发展过程
适切与适合、合适的意思比较接近。近年来教育中的新理论多起来,不合适的感受也多起来,这几个词语就经常被使用。使用它们似乎无须解释,它们显然是被作为共识的词使用的,事实果真如此吗?记得陆有铨先生曾经说,教育没有最理想的,只有最合适的。我认同他的这个说法,还多次以合适为题写过些讨论教育改革的文字。我认为他的这个说法很实在,用它来解释教育很通俗也很朴素。然而讨论教育改革,可能还需要些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因为改革这个词,意味着要改变些什么、革除些什么、建设些什么,所以就有个除旧布新的问题,有个由旧的合适改变为新的合适的过程。更确切地说,改革是个发现并确认旧的不合适,而后导引其走向新的合适的过程。这就绕不开一个必须达成共识的前提,讨论改革过程中的合适,究竟是谁适合谁?谁与谁适切?
俗话说鞋子是否合适只有脚知道。但是,导引其走向新的合适,这就不只是个谁知道的问题,还有个谁适合谁的问题。而谁适合谁,并非就是简单的事实,适履的办法显然是迂腐行不通的,但如果说“穿几天就合适了”,这与削足适履或者“改履适足”相比较,就比较复杂,也不能简单化地作出判断。课程改革之初我们的许多做法,就常常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总试图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断,也就总会陷入双向两难的困境。究竟是教学适切于课程还是课程适切于教学?是常态适切于改革还是改革适切于常态?是实践适切于理论还是理论适切于实践?这或许只是些“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今我们可能就不会如此简单地看问题了。我们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宣言上,的确都经历了一个“渐”的过程。
正是这个“渐”的过程,让我们体验了适切,也让我们能够重新思考适切一词应该如何解读。“渐”是一段时间的流程,也是空间的延伸,它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谁适合谁的问题。这不是人们各执一词的论争能够解决的,而是有赖实践解决的。实践不只是改革的对象,它还是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实践承载着改革,实践其实就是改革自身。适切,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显露的还是隐蔽的,事实上终究只能在双向互动中发生。在此期间的各执一词的许多论争,可能犯了个共同错误,误以为自己始终坚守,许多为适切而发生的改变,都是他人在退守,没能觉悟到自己也在改变。适切是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改变就在双向互动中发生。这个过程时下还在延续着、拓展着,也继续被实践检验着。
为何适切:素质教育与考试竞争的困惑
我们为什么要改革?不能只说“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得说教育的道理;说教育的道理,不能只说培养杰出人才创新人才,还得说具体的基础教育的道理。这就必然面对基础教育中的素质教育与考试竞争问题。
就课程与教学改革的适切性而言,这称得上是个边缘性问题了。但这个边缘性问题其实不边缘,因为许多实践者正是被这个问题困扰,疏离了课程与教学改革,让我们为课程与教学改革所做出的努力,都变得无足轻重了。一位资深实践者说,我们其实不关心课程,我们的领导,我们领导的领导,也不关心课程,他们只关心考试成绩排名、名校录取的人数。我不是危言耸听,每年高考之后,有谁关心过我们教的什么课程,课程是否改革了?设置课程是你们专家的事,我们只管学生考好,只管课程适切于考试,就是让我们教《古兰经》,我们也照样教。就此而论,课程与教学改革的适切性,可能不只是个课程怎么改革、教学怎么改革的问题,而是个为何改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教学评价。
这就要回到“基础教育”上来讨论问题。基础教育是什么性质的教育?它与高等教育这种专门化教育是什么关系?弄不清这个问题,或误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改革的适切性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与基础教育适切,或与误解的基础教育适切。辨不清这两种情况,课程与教学改革就会因为盲目而变得扑朔迷离。我在《合格性评价:基础教育评价的应然选择》[2]中,论述过基础教育的方向偏差及改造对策,我认为方向偏差是选择了顶线评价,改造对策是实施底线评价或者合格性评价。顶线评价背离了基础教育的本分,混淆了它与高等教育的区别,违背了高等教育要支持差别原则对均等机会的优先性,基础教育要坚持均等机会对差别原则的优先性[3]的教育法则。如今我依然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讨论课程与教学改革的适切性,其实无异于不着边际的自说自话。
因为这是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宗旨,也是讨论适切性的依据。基础教育要培养人的普遍适应性的基本品质,培养专门化人才是高等教育的事。如果让基础教育越俎代庖地去做高等教育的事,自作聪明地弄成高等教育的预备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如何还能适切?许多基础教育学校,不关注培养人的普遍适应性的基本品质,只关注几门考试课程,还把课程评价结果标榜得很夸张,把获得到大学里学习的入场券,说成成功、成才、杰出人才。基础教育因此陷入素质教育与考试竞争之间的困惑之中,改革到底是为着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还是为着应对考试竞争?这也正是课程与教学改革为何适切的困惑。
为何适切的困惑,有个“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教育背景。我认为这个背景造成的认识偏差,是改革遭遇不适切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提法不合逻辑,它把教育评价和教育目标并列起来,弄成了两者非此即彼的关系。这就导致了一种误解:要考试竞争就不能实施素质教育,要实施素质教育就不能考试竞争。这样的误解很危险,它让正常的考试竞争异化成了恶性的“应试教育”,也以某种隐蔽方式抵制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可以想见,在寻求课程与教学改革适切性的时候,谁能不为如此严峻的“转轨”感到困惑?因此也就谁也弄不清应该为何适切了。
要寻求课程与教学改革的适切性,必须遏制考试竞争异化成恶性的“应试教育”,关注提升国民素质,否则改革就可能被架空。任凭僵化的尖子主义盛行,考高分进名校的狭隘目标,就把基础教育窒息在选拔淘汰的漩涡里了。在这种情况下,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法,就可能成为教条,而实践素质教育,也就很难在实质上有所作为。近年来基础教育中发生的许多恶性事件,都与恶性考试竞争制造的压力相关。人们质疑学生的心理健康有问题,是回避了主要矛盾,事实上这主要是教育评价出了问题,是正常考试竞争异化成恶性“应试教育”的问题。值得辨析的是,谁该对这问题负责?至少可以认为,凡以恶性考试竞争结果评价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学生的做法,无论是炒作,还是歧视或者漠视,都是在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也是在以隐蔽方式抵制实施素质教育。
人们为“应试教育”辩护的唯一理由,是所谓的培养杰出人才。但我们不能不提醒人们,有些“杰出人才”的发展可能比失败者更糟糕。因为“应试教育”很难保障他们可持续发展,他们未必热爱自己的专业,还可能因为竭泽而渔失去学习兴趣。新近某著名高校淘汰大批在校生的事实,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而有学者说某著名高校“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更令人忧虑。我们真该认真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了,大家不遗余力地通过恶性考试竞争成为“杰出人才”,究竟是要肩负更大的社会责任,还是要获得某种特权?教育如果在背离素质教育的歧途上行走,如何能养成人之为人必需的素质基础?
课程与教学改革适切性所遭遇的真正的难题,不是我们缺乏“改革”的条件,而是缺乏遏制“不改革”的条件,也就是遏制追逐恶性考试竞争、无视人的基本素质的条件。有关课程与教学改革适切性的讨论,不同程度地忽视了为何适切。而我认为讨论改革的适切性,必须首先关注它究竟是否与“基础教育”适切。
为谁适切:优质教育与弱势群体的讨论
我们为谁改革?改革的适切性是为了谁的适切?不能只说与“基础教育”适切,还得说与基础教育中的哪些人适切,还得说与基础教育的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教师、每一个学生都相关的道理。这就有个如何面对优质教育与弱势群体的问题。
这似乎也是个边缘性问题,但这个边缘性问题是被边缘的。在讨论课程与教学改革适切性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听不到弱势群体的声音,他们是否被边缘化了?前述的那位资深实践者,他说他并不关心课程,只关心学生考得好,只关心考试成绩排名、名校录取的人数。如果换个角度看,那些与高考无缘的,成绩排名靠后、名落孙山的学生,是否更需要关心?他们的同样付出心血的老师,是否更需要理解?这是不知道为何适切的悲哀。如果再换个角度,看看那些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他们就读的学校、任课的教师,许多人连这样的“不关心”、“只关心”的机会也未必享有,他们还在争取保障受教育的权力,渴望教育无歧视!这就是不知道为谁适切的悲哀了。改革的适切性,因此有个与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教师、每一个学生适切的问题。
与“基础教育”适切,这个提法比较宽泛,课程与教学改革的不适切往往很具体。课程的深浅难易,是个为谁适切的问题(在教学层面,深浅难易的不同回应,可能是个如何适切的问题)。有人说新课程太浅太易也不难驾驭,但如果依据新课程标准教学,又不足以应对考试竞争;也有人说新课程太深太难驾驭不了,适切性呈现出如此巨大的落差,意味着改革的复杂性。这样的落差不是修正课程所能应对的,逐层实施教师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也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是为谁适切,如果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很难从实际出发进一步解决如何适切的问题。
教育中鼓励拔高的取向,关注的是所谓优质教育,这造成了教育资源的集中与短缺。梯度发展、高位均衡、优质拉动薄弱的取向(与特色发展不同),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薄弱。俗话说,装睡的人叫不醒。把优质教育资源集中起来办名校,偏偏被炒作成名校培养优秀人才。有三六九等的学校就会有三六九等的人,课程改革奢谈普遍意义上的适切性就只能是乌托邦。要想让乌托邦变成现实,必须要换个角度想问题,优先关注弱势群体是否适切,唯有这样的“为谁适切”,才能真正解决“为何适切”问题。
这里的优先关注,是基于一种简单认识:讨论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适切性,只考虑适切于普通高中教育、普通高等教育是不够的,还有一份对中职教育、高职教育、适龄者成为工人、农民、农民工等的继续教育的责任。为了这份责任,所以要优先关注弱势群体,优先考虑弱势群体的教师和学生们是否适切。
值得辨析的是,这样的适切性是否会对优质教育群体不公?这其实是种误解。因为所谓优质教育群体,主要是依据选拔性考试评价判断的,这未必是基础教育的完整性评价。而基础教育的课程与教学改革,不是选拔性考试评价课程的改革,而是完整性课程体系改革,在这样的改革看来,所谓优质教育与弱势群体,未必有人们炒作的那么大的落差。如果我们是要培养学生的“负责公民的价值观、态度与情感、认知技能与非认知技能、创造性与行为能力”,这显然会有益于弱势群体,但也未必就对优质教育群体不公。
课程与教学改革,应该在完整性课程体系中寻求适切。但人们讨论改革的适切性,鲜有讨论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课程的,这是一种失误。这种失误窄化了为谁适切的意义,忽视了被优质群体的薄弱,也未能充分尊重弱势群体的优质。
从关怀弱势群体的角度,判断改革是否适切,需要公正的教育评价。譬如他们中的贫困生,贫困生中的进城务工者子女,留守农村的孩子,他们以稚弱的肩膀担起生活责任,以稚嫩的童心宽容生活境遇,我们到底该如何评价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与情感?有研究证明,像这类国际公认的优质教育发展指标,与地域经济发展水平无关,许多薄弱学校学生的发展,还可能高于优质教育学校。再譬如他们中的学困生,他们完全有条件学会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学会动手动脑、生存生活、做人做事,如果实施合格性评价,同等评价他们的道德、体育、劳动等全面课程,他们就未必还是学困生。如果只是几门选拔性考试课程,制造了他们的学困,这就是教育评价出了问题,却让善良的孩子们承担责任!因此,讨论课程与教学改革为谁适切的问题,必须公正对待薄弱学校或弱势群体的学生。
从关怀被优质教育群体的角度,判断改革是否适切,同样需要公正的教育评价。譬如他们中的有些学生,陷在德育空泛、体育敷衍、美育功利、劳动教育如同虚设的唯考试成绩至上的误区里,就可能失落负责公民必须的价值观、态度与情感。仅就认知技能和创造能力培养而论,如果改革与考试竞争不适切,还有个是否与人的可持续发展适切的问题。改革如果是为学生们夯实全面基础呢?这是适切还是不适切?有人把中美两国的教育进行比较,说我们的基础教育是基础好,他们基础差,说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创新思维差,他们是创新思维好。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在褊狭的“基础好”与全面的“基础差”之间,我们又该如何判断?我们的教育思维需要转变,讨论课程与教学改革为谁适切,这对被优质教育群体的学生而言,还有个为之计短浅还是为之计深远的问题。
如何适切:文化选择与方法选择的解释
任何国家和地域的文化都是独特的,任何学科的课程与教学都是具体的。这让我们逐渐明晰了一个道理,寻求改革的适切性,这不是创造插花艺术,它得守护自己的根本,它得存活于具体的课程,它得创造实实在在的教学生活。
我们对课程与教学的认识原本很清楚,是各执一词的课程论和教学论,把我们清楚的认识模糊了。但我们的教学实践,并没有完全被理论左右,它还在按部就班地前行,似乎依旧秩序井然。这里可能存在着一种文化选择,这种选择是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发生的,这种选择其实就是在寻求适切,寻求改革与特定文化传统之间的适切。
课程论与教学论是并列的学科。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课程标准与教学大纲、教材与教科书,是几对并列概念,辩论它们的高低上下没有意义,但它们的旨趣之异值得辨析:课程论关注教育的物质性、结构性、科学性,可以预设也易于科学评价;教学论关注教育的行为性、过程性、艺术性,不容易准确预设也难以科学评价。这样辨析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文化选择:以发展为特征的文化,重视教学什么胜过如何教学,就会较多关注课程;以稳定为特征的文化,重视如何教学胜过教学什么,就会有重教学的传统。我国古代,如果说编五经的孔子和撰四书的朱子是课程大师,历代名师就是教学大师了,这体现的正是我们重教学的传统。如今,我们为寻求发展而重视课程,这自然无可厚非,但这也正是我们课程改革的艰难所在,因为我们不能自欺欺人,无视自己重教学的传统。
我们寻求课程与教学改革的适切性,因此要承认课程改革的艰难,重视教学适切,让课程改革中的教学适切,成为改革的文化特色。譬如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是德育为先、文以载道、教学永远具有教育性的特色;韩愈说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这是讲究教学民主,以为师之道建构教师尊严的特色;而如“教学有法,法无定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教学主张,则是尊重教学自由,释放教学个性的特色……我们的课程改革,是否该弘扬这样的特色?这既是教学适切,也是文化适切。
这样的适切,不会影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会影响有益的借鉴。借鉴的意思是借镜,不是异地移植;借镜的功能是比照,不是在镜子上谈理论,更不是要撞进镜子里简单模仿。寻求改革的适切性,论借鉴只能是继承中的借鉴,这样借鉴才能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也才能依照改革的精神走自己的路。所以我认为,从文化选择的适切性来看,寻求改革的适切性,我们应该审慎地改革课程,宽容地释放教学自由,因为我们的课程文化相对稳定,不容易轻松颠覆,也不宜奢谈重构重建,我们的教学文化很灵动,它一直就在生机勃勃的变革中。而实践中的有些做法就让人担心,人们粗制滥造地编制特色课程,还采用划一的教学模式限制教学自由,如此扬短避长,如何能寻到改革的适切性?
不同学科的课程不同,教学也不同,寻求改革的适切性,因此要重视学科特征。这在以往的理论或实践中都比较清楚,文科不同于理科,文科中的语文不同于历史、政治,理科中的物理不同于化学、生物,它们都不同于艺体、劳动各学科。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如今有些改革的理论、改革的实践,模糊了学科之间的界限。无论是言之凿凿的理论论证,还是声情并茂的课堂教学,忽视了不同学科的特征,改革如何还能适切?
以往我们总担心过细的学科分化会造成学科壁垒,如今却不能不面对不同学科间的“混搭”所造成的实践者的尴尬了。有些理论研究,却让文科和理科共享同一种教学模式或方法,有些研究者,硬把外国的理科课程改革模式移植过来改革中国语文,实践中能行得通吗?或者它压根儿就没考虑实践?这样的研究如果不被理论拒绝,是理论脱离实践,但这样的研究如果不被实践拒绝,就很可能是个实践以理论作装饰的问题了。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时下有些课程与教学改革理论,其繁荣的形式,是否遮蔽了实质的贫困?而随处可见的那些粘附在课程与教学改革、课程与教学创新上的理论基础、理论依据、理论解释,是否可能只是些生吞活剥的标签、符号?
课程改革尊重不同学科的特征、区别不同学科的教学,这是个具体的适切性问题,不能把它边缘化。改革中的一些新模式或者新方法,仿佛各学科都可以拿来用,这就避免不了牵强附会,还空谈什么适切性?当年布鲁纳提出发现法教学,曾经解释说它适合理科或者科学课程,还说它不适合历史等人文学科,但我们今天的改革中,偏偏就有人把探究教学的方法,拿来实践中国语文教学,无论是虚假的行得通,还是真实的行不通,这里都该有些深层问题值得思考。虚假的行得通是自欺欺人,这里欺的不只是改革的适切性,而是课程与教学。真实的行不通是实事求是,这里所求证的也不只是改革的适切性,而是不同学科课程的不同教学在人的发展中的不同价值与功能。
我认为我们的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中,中国语文是个最活跃的学科,但也是最让人不踏实的学科。因为中国语文以及中国历史等学科,与外国的同样学科就有根本性的文化差异,与他们的理科或科学就更有天壤之别,这里不只是课程不同,教学也有各自的特色。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花一番工夫,研究中国语文等学科传承几千年的课程与教学的特殊性,以此来寻求其改革的适切性,也收获它们在人发展中的不同价值与功能?
课程改革的适切性,落实到教学上来,不是个简单的课程实施问题。我认为这里需要有个一定之规的法,还需要释放万般变通的式。如果没有一定之规的法,改革就谈不上改革;不能释放万般变通的式,改革就谈不上适切。如果硬是把成千上万的教师捆绑在一个模式、程式、方式上,这可能不只是僵化迂腐,而是要用形式主义害死人。它漠视或轻视教师与学生的适切,这无异于是有意无意地要遏制改革。
就方法改革的适切性而言,“教学有法,法无定法”是个优良传统。这句话前面的两个法字是“法”,后面的法字是“方”或“式”,它的意思是教学有法而法无定式。“法”是一定之规,具有普适性的特征,而“方”或“式”是依法行事的样式,具有复加文饰的或者个性化的特征。那么,如何解释课程与教学改革中的“法”与“式”?有些关注实践的理论者常说“不要空谈理念要谈实践”,有些不关注理论的实践者常说“不要讲为什么,只要告诉我们怎么做”,这两种典型的经验思维论,存在一个共同的认识偏差,这就是误解了改革的思想、理念或观念。我认为,改革的思想、理念或观念就是改革的“法”,是改革的一定之规,具有普适性特征;而所谓谈实践、怎么做,则是改革的“方”或“式”。改革的适切性,最根本的正是“法”要适切,而“式”则完全可以释放开来。
就“法”要适切、“式”可以释放而言,改革过程中发生的诸多困扰、冲突、论争,由此造成的诸多不适切,都可能与误解有关。而误解并非只是来自改革的质疑者,也存在于改革的支持者中。为此我们有必要提出两个普适性的问题,尝试进行些解释,以求在“法”的适切性上,能达成共识。
一个问题是围绕着教学方法的“教学”,发生了要不要教、要不要教知识、要不要教书本知识等的质疑,这是误解了探究学习、自主建构、知识的生成性等等。其实教学毕竟不是自学,即便说重心在学,也依然是有教之“学”,如果只论学而不论教,就是论学习而不是论教学了。所以课程与教学改革中主张的各种各样的新方法,都是教的方法、教学生学的教法。教法不排斥以儿童为中心、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因为这只不过是高水平的教法;教法也不排斥直接经验,而以间接经验和书本知识为主,只是因为这是人的经验传递的特殊性。值得解释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国的发现法、探究法为我们的中小学教学方法改革所关注,人们学习这些方法,移植这些方法,得益于这些方法,但由于承载这些方法的学习主体是学生,关注的重心是学生,方法的宗旨也是学生,人们很容易忽视它是有教之学,也就未必都能确认它们是教法,这其实正是这样的教法的高明之处。
另一个问题是围绕着教学方法的“方法”,发生了新模式、新方法、新范式是否合适的质疑,这可能是误解了交往、对话、合作等等。其实教学的“方”或“式”,最是不能刻意打造,最是需要循其自然的。课与课不同、教师与教师不同、学生与学生也不同,规定教师讲课不能超过几分钟,学生合作学习不能少于几分钟,提问学生不能少于多少人,还要牵强附会地在课堂上实现诸多教学目标,这哪里还会有真实的教学?就方法的适切性而言,我认为只需要追寻教学的新思想、新理念或者观念,而无须僵化的程式或模式。心灵沟通可以是交往,倾听可以是对话,默契也可以是合作。如果不刻意、不打造,就把循其自然作为教学方法之“法”,适切就不会有什么阻碍,因为在课程改革一定之规的“法”的条件下,教学完全可以不必太精致,不必过分包装,也不必把简单的东西弄得很夸张。
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应该尊重人发展的自然秩序。每一个儿童都是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所以教学应该尊重儿童发展的自然秩序,尊重它、循循然地适合它。所谓课业负担的实质其实就是心理负担,它是课业与儿童心智发展自然秩序不适的产物,还是这种不适所负载着的成人压迫力与儿童承受力冲突的产物,它是成人违拗自然秩序制造出来的。每一个教师同样都是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教学也应该尊重教师发展的自然秩序,即使是教师专业发展中的科学与技术、教学基本功训练,也无须刻意打造。教师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史,自己的志趣偏好,都应该得到尊重,让每一个教师都有属于自己的教学个性或风格。
作者简介:杨启亮,男,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南京 21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