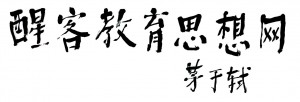董云川:大学已经染上了一切世俗社会的坏毛病
作者 | 董云川 发表时间 | 2013-07-15 来源 | 醒客教育思想网(作者授权文稿)
未来若干年,中国大学管理的观念、理论与实践势必在教育规律与行政主导和经济制衡的博弈之中艰难地行进,进步势在必然,障碍在所难免。国际化概念会普及但操作大多对接无门,理论成果层出不穷但缺少本质意义的突破,而管理实际行动的功利取向将有增无减。
[原题:在博弈中蹒跚的中国大学管理:概念、理论与行动]
中国现代大学的生长与发展是蹊跷无序的。既难以琢磨,更难以预测。作为兼具多重属性的高层次文化组织,大学的生长与发展虽复杂多变,但理应遵循一定的轨迹和规律,应该可以依据历史条件、文化背景、经济基础和时代特征加以认识和把握。然而,不幸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无论是宏观政策的制定者还是中观层面办学的操控者,直至其间微观个体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大家均对大学的存在和所作所为持有疑虑,对于大学中存在的种种现象,包括教育教学、领导管理、科学研究、后勤保障及其相关的竞争手段、发展策略等等问题,非议众多,莫衷一是。在体征庞大、欣欣向荣的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中,不同程度存有失语甚至是集体迷茫的现象。
仅从管理的角度来看,作为文化组织的高等学府,在计划、指挥、控制、激励、协调、实施等职能环节之上均难以做到规范而有序。规划可以束之高阁,指挥可以多头并举,控制可以时紧时松,协调可以跨越逻辑,激励的主体动因已经不再是学术本身,而行动的实施可以将教育与文化的“道理”置之度外。至于谈到管理的核心要素“人”,更是问题丛生。对校长的任命可以不考虑院校发展战略的连续性而只需要顾及行政权力或任期的平衡;作为学科学术运行实体的院系已经干净彻底地蜕变为一级行政组织,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学科带头人大多已演变成为在各种资源的泥潭中左冲右突的中层干部;再往下,具体的每一个研究者和教育者对于教育本质和学术意义的坚守已经成为无奈之举且岌岌可危了。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加强管理的呼声日渐高涨。管理体制改革的说法多样,但做法陈旧,各式各样的管理改革范例多多,而本质上的突破并未出现。中国大学的管理改革犹如在同一条道路上背负着重担绕圈子,背篓里的改革产品越来越多,而奔跑的方式并未改进,更苦、更累、效率更低。奇怪的是,虽然大学内外各种相关人群都各有苦衷,但许多人仍旧对如此的管理现状津津乐道,还有人乐观地认为,中国大学已经步入现代大学制度的康庄大道。对此,本人的判断是:现代大学制度曙光乍现,但目标的实现仍无时间表。
以下仅从大学管理的角度针对“概念”、“理论”和“行动”三方走势做初步辨析,以为同仁商榷:
概念的国际化
概念将越来越普及,交往会越来越频繁,但实质上的运行仍然无法对接
撇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与国际惯例相当的中国现代大学雏形,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全盘照搬苏联教育模式不谈,最近一轮与国际接轨的苗头始于30年前拨乱反正的全新历史阶段。其时,深受闭关锁国危害的中国高等教育迅速复兴,历经各种“运动”磨损的中国大学犹如枯木逢春,在追赶“大趋势”和面向“地球村”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吐故纳新,不仅恢复了元气,而且迅速繁荣壮大。其间,专业学科、学制学分、学衔学位、组织机构、院系职能以及课程模式等相关称谓迅速国际化,人们在大学内外所提到的种种概念无不以国际称呼同一。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际化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从形式上看,中国大学早已栖身国际高等教育大家庭,与世界大学共享着各种各样的教育概念与学术称谓。许多人认为,照这样的趋势,中国大学很快就能成功地与国际接轨了。
然而,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大学与世界其他国家大学,特别是发达国家大学相比较,仍旧是形式上的一步之遥但本质上是失之千里的。除开常规意义上的发展要素之外,中国大学所遵循和奉行的生存法则与众不同,这就使得中国大学在生存与发展的竞争中所面对和依赖的博弈要素与世界大学迥然各异。原因在于,中国大学基本上仅只是一种形式上仿真的文化存在,其并非主要为了学术的发生发展而存续。在大学里,校长是官员,学科带头人是干部,博导是一种权力,教授是一种待遇,人才依赖指标衡量,在职教育变成文凭交易,“大学”比“学院”更高级,高等学校被分别界定为副部级至正处级单位;能不能成为教育家由组织部说了算,能不能立项做研究由行政部门说了算,能不能成为学术大师由局外人说了算,专业学科的调整由计划主管说了算,职称岗位的设置由编委和人事厅说了算,就连“优化”课程设置的框架都需要由上级钦定。更有甚者,传统的行政干预通通成功转型,一律演变为专家评审,掌握各种资源的主管人员们纷纷摇身一变,扮演起专家或者遥控专家的角色;大学中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一应俱全,但并不享有决策职能,能够发挥一点点咨询作用就足以让教授们感激涕零了。近日,“天津大学龚克校长明确表示,学校将对学术委员会进行改革,人员要在教授真正推选基础上产生,在学术建设上要把权力交还给学术委员会。他认为,目前包括天大在内的许多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几乎成为学校决策的一个附属机构”;“2005年11月19日,赵启正卸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从正部级“降级”接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其间他提到:‘院长是什么级别之前我根本没想过。他们给我的聘书上在院长后面有个括弧,写着正处级。’”这仅只是当代中国大学黑色幽默之九牛一毛。报道者李松同时称:“官本位是中国教育不能承受之重,是中国高校难以成为世界一流的最大障碍”。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内外大学之间,学生可以交流、学者可以互聘、专业可以合作、学分当然可以互换互认,但我们必须清醒:换进来的除了虚名就是概念,而换出去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学费和人才。发达国家大学真正需要的是作为个体的、聪明勤奋的学术人才和作为经费来源的广阔教育市场,至于我们的大学制度与他们对接与否并非考虑重点,而且,如果我们的教育制度越落后,他们就越有可能从中国摄取更多的教育资源。
究其根本,中国大学之国际化,尚有两大先天不足:其一是无根,即本土化、区域化、个性化不足,因此缺乏平等的对话资本;其二是无性,即作为文化组织的独立性不具备,缺少大学跨国界沟通对话最根本的接口——自由之学术和独立之精神。因此,在非教育非学术之多重外力作用之下蹒跚前行的中国大学,无论有多少人用多少时间耗费于国际语言的学习之中,由于在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式和科学研究等领域大相径庭,必然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英语可以普及,但言语的内容和教育、学术的内涵还是难以对接。
因此,可以预见,未来若干年,国际化仍旧是一个概念上的香馍馍。概念的引入会越来越普及,人们的话语方式会变得越来越西化,制度形态亦会逐步仿真而向西方大学靠拢,院校符号系统将会全面照搬,但是,由于教育管理制度体系最底层的游戏规则没有改变,所以无论外部的改革呼声喊得震天响,根本上还是入口不入心、见首不见尾的。所以,本人以为,中国大学的国际化已经发生,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办学格局将难以成型,除了越来越频繁的友好往来和教育资源的争夺战,所谓“国际接轨”依旧遥遥无期。
理论的复杂化
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转型期的矛盾,导致两全的尴尬和应景的学术
理论的繁荣景象跃然纸上。近十年,中国人写出来的论文和所谓的著作,在数量上足以比肩于数千年文库总和,但是,有思想、有影响、有突破的著述及流派却凤毛麟角。成千上万的管理论文专著内容大多交叉重叠,少有新意,对管理事实的总结往往是马后炮,对管理规律的探究往往在兜圈子,对管理现象的追踪往往流于表面,更缺少周期性的经典管理试验成果。纵览国内外教育管理研究领域,无论是三阶段说,四阶段说还是多阶段说,过去一百年教育管理理论的变迁趋势是指向人性化和复杂化的。基本的脉络始于古典教育管理理论以效率为本的模式,发展到人本教育管理理论以人为本的模式,再进步到科学教育管理理论以理性为本的模式,直至现在归结于后现代教育管理理论以多元整合为特征的模式。由于历次运动造成的断代,中国大学的管理理论变迁逻辑大体与国外相当但无法同步,从研究所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变化轨迹上看,至少延迟了三十至五十年。
深层问题存在于理论与政策的关系微妙,教育规律、管理法则与时政方针之间存在多元的博弈冲突。管理理论往往并不来源于管理实践及其发展趋势。近年来流行的宏观体制改革、机制创新、高校内部管理改革、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教育科研管理改革、后勤管理改革大多不是源于理论研究的指导而是策动于大学外部各种政策力量博弈之后形成的行政指令,而管理政策的制定似乎与管理理论研究也没有直接相关。也就是说,管理现实往往是文件通知安排的结果而非理性发展的结果。表面上看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广泛吸纳了最新的管理研究成果,然而不幸的是,这些管理研究成果恰恰是在既定政策框架的基础上所研究出来的。这就步入了一个怪圈。理论的产生违背了基本的科学逻辑,由此产出的管理研究成果成为制定朝令夕改之政策的注脚。换言之,理论研究无法影响政策制定,注定了理论本身价值意义的流失。
另一方面,管理理论的研究大多并不指向于管理现实的改良,而仅仅是为了满足“课题”、“项目”、“评奖”和“晋级”的需要。因此,严肃的管理科学研究变成了轰轰烈烈的“立项”运动,重申报不重孵化已成为普遍现象。谁也没有耐心和机会去选一所或者多所高校来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周期性的漫长的全过程试验。即便有,也是各级政府和学校树立的示范工程,仅仅满足于表面化、短期行为和政绩指标,而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的顽症难题,并无触动,更无本质意义上的创新和改良。在这样的情形下,无论是个人还是高校,所谓的管理理论成果层出不穷,但管理规则本身仍旧我行我素,铁板一块。非教育特征、泛行政化、低效率、高成本、部门林立、冗员过剩、浪费惊人、服务能力不强、管理水平不高的事实并未因为“理论”的繁荣而受益。
问题的根源更在于管理理论探究者们的眼光很难专注于管理现象本身,而不得不紧随那些驱动管理行为的控制者的好恶。大的逻辑是:中国大学是行政科层金字塔之中的一个基层单位,管理研究是在这个既定框架之下的探索,如若超出这个范围界限,那么,无论何种理论观点还是操作模型,大多会被冠以“不现实”的帽子而发表无门,既无法立项,更没有谁会给你试验的机会,于是乎,研究要么无果而终,要么只能束之高阁,孤芳自赏罢了。
事实上,管理研究的主导话语大多被当权的管理者们所垄断。这些在既定的管理制度体系下的既得利益者们同时拥有行政头衔与学术头衔,许多既是课题立项的组织者又是课题申报者,还兼具评审专家的身份。当然,制度形式的设计是公正而避嫌的。因此,总是在各种评审之前做好规避工作,一般通过交叉评审来实现形式上的公正公平。在如此情形之下,聪明的学者大多选择两全之路:首先“识时务”而追随资源的操控者,心甘情愿地替既定政策作注,从而获得丰厚的研究经费和相关资源,继而,力所能及地开展一点真研究,触动几个真问题,探索一下真规律,写出几句真思想。其间一旦出现矛盾,就动用精巧的中国式文句加以调和,创造出诸如“统筹兼顾”、“数量与质量并重”、“当前与长远相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国情与国际融会贯通”等许多翻译之后让外国人“晕菜”的复合型表达方式。这样一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显然就成为了两全学者们认为的中国大学管理改革最好的出路。这种曾被本人称之为“现在大学制度”的管理体系常常把大学根本的属性“自由之学术和独立之精神”撇开不谈或从属于其他原则之下。说白了就是:即便国际通行的先进的现代大学制度是那样的,但是,中国的大学就只能是现在这样的。而由于中国现代大学管理体系是与众不同的,因此,我们的大学制度当然就是“创新”的。
这种莫名其妙的逻辑被许多人认可从而在管理研究中十分盛行。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产生的理论成果无论有多少,都将在“两全”和“两可”的博弈之中流于圆滑而陷入尴尬的境地。当然,繁荣研究景象之下苍白无力的成果也具有客观的障碍,那就是转型期的矛盾、价值的多元化以及文化冲突的必然。有了这些客观原因,我们就可以在未来的一段时期里,堂而皇之地为惟上媚俗、随波逐流、附庸风雅的理论研究找到下台之阶。
行动的功利化
“潜规则”的存在与普遍的后台操作,导致知行两分,造就“识时务”的俊杰
无论理论研究是多么地喧嚣,成果汗牛充栋。大学管理的操作现实却是完全冷静、理智而“识时务”的,实践与行动的路径与理论成果几乎不搭界。有如本人在十五年前的预言:就像铁路之两条轨道,并驾齐驱但永不交合,各走各的路。历经“九·五”和“十·五”的规模扩张,进入“十一·五”不得不关注质量的时期,情况并无根本改变。管理理想与管理现实之间的鸿沟在口号上常常是统一的而在行动上却愈加疏离,在未来的时日里,远大理想与严酷现实之间的博弈冲突仍将继续。
比如:官僚化在管理研究中是被批判的,而在管理行动中是被推崇的;寻租行为早已被管理研究所揭穿,而在管理现实中大行其道;科层体系的弊端已经一目了然于管理教材之中,而在管理现实中却拥有越来越广泛的维护者。今天的大学已经染上了一切世俗社会的坏毛病,更可悲的是象牙塔之中的生灵们对此大都津津乐道,而且乐此不疲。
张楚廷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上级批评说高等学校不安于定位竞相升格是盲目的,其实不然,他们都是主动且理性的!”因为在当前管理制度体系和运行方式下,真正的理性定位是会失去机遇和资源的。而“跑点”、“跑项目”、“跑基地”等一系列为教育管理理论所不齿的行动却反而是十分有效又有利于学校发展。因此,无论是学者要搞点研究,学科要布点发展,学校要扩大办学,都不得不做出“明智”的选择,即便这种所谓明智的选择与开会时的誓言和政策文件的理想相去甚远,亦义无反顾、在所不惜!李侠对此亦有精辟的分析:“大学内在的价值理性在窘迫中早已遗失……在艰难的选择面前,大学何为?是把自身定位为一所思想独立的大学还是一个官僚机构?如果想成为思想高地,又担心来自经济方面的隐忧;如果把大学完全定位为一个准政府机构,又与公众早已接受与认同的大学理念相矛盾。在这种基础性的两难困境面前,大学别无选择,只能首鼠两端,见风使舵,或者干脆以牺牲思想独立性为代价,在市场机制的操作空间内向权力投降,退化为精神的侏儒,完全按照官僚机构的模式构建与运作。”近年来,关于一些高校中著名学者、教授、博导积极竞争校内副处以上岗位的奇闻轶事不断见诸报刊,足见大学内在品性与外在价值认可之间的不平衡。
高等教育的功利性原本没有错。错就错在当前的逐利行为远离了教育活动本真的意义,包括人性的生长、文化的发展、科学的进步、自由的学术、独立的品格以及真实有效的管理。而将错就错的行动取向还根源于人们对于“潜规则”的普遍认同和对“后台操作”的集体默许。彼得·杜拉克说:奖励什么,就得到什么。因此,当前盛行的“趋利”、“短视”、“虚浮政绩”以及大面积庸俗化的“关系往来”等违背教育及学术规律的流行运动归根结蒂还是管理政策引导和变相奖励的结果,与此同时,也是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同角度的人群集体纵容的结果。领导们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2007年9月9日,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北京语言大学45周年校庆期间举行的“社会文化建设与当代大学的责任”论坛上,对大学的功利化倾向提出了批评。他分析说,功利主义太重,就会急功近利,急功近利就会学术浮躁,这就导致揠苗助长、造假抄袭现象屡有发生,大学文化积淀薄化。他还认为,大学的官本位倾向也在影响着学术的发展,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也就会逐步失去色彩。
当今时代,多角度、多渠道、多种成分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涌入大学,与落后的教育资源配置和大学管理体系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深究下去,教育资源配置取向与管理制度设计主旨的不协调甚至背道而驰正是批量生产“识时务”之“俊杰”的主要动因。对于这种惟妙的、虽不正常但通行无阻的现象,人们很难在政策表述上找到破绽,正如文前分析的那样,许多政策都是“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统一”的,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时过境迁的。所以,现行管理制度本身并不能有效规避之,反而不断纵容“知行两分”的行动。于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必然成为中国式管理的最有效行动准则。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几千年的封建陋习全面渗透浸染于大学之中,跌宕了百年的中国现代大学想要涤荡清除之,谈何容易,尚需假以时日。未来若干年,中国大学管理在观念上、理论上与实践过程中还将面对教育规律、文化法则与行政主导、经济制衡等生存要素之间尖锐的博弈冲突,发展进步势在必然,障碍重重在所难免。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作为文化人的学者、作为文化载体的学科以及作为文化组织的大学,能否从世俗的泥潭里挣扎出来,唤回点滴“文化自觉”,少一些“失语”和“失范”的行为追求,当高等教育系统内外有更多的同仁能够视“自由之学术和独立之精神”为大学的价值轴心,且越来越多个体之文化自觉行为连成片的时候,现代大学制度的蓝图就会呈现。
这一天值得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