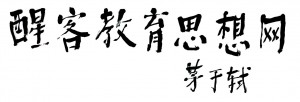--梁文道与周保松对谈
作者| 梁文道 周保松 时间 | 2010-06-01 来源 | 梁文道博客
【读者好】周保松是我的老同学,不仅在同一个系上课,而且还一起拜在石元康教授门下攻读政治哲学。只不过他是一个比我好得太多的学生。当年我读了四年硕士都没唸完,他却在硕士毕业之后跑到伦敦政经学院取得博士学位,然后回到母校任教政治与行政学系。
可是换个角度看,他却又是一个十分反常的人。原来他本科唸的是工商管理,一个人人称羡的热门行当,前途不可限量;但他竟在大三那年忽然转系哲学,一个在另一种意义上「前途不可限量」的学科。不只如此,他从大一开始加入《中大学生报》,写一大堆批判校方、批判主流社会的文章,这也是一般工商管理学生不会干的事。
最神奇的事还在后头。始执教鞭,他就开了网上讨论班,和他的学生大谈政治、哲学与人生,而且谈得十分严肃深入。前几年,他把第一批讨论成果编成《政治哲学对话录》一册,约五十万言,自费印刷三百本,留给同学当纪念。要知道,在教授都成了论文机器与行政人员,劳形于资金申请与工作报告之间的今天,还肯花这么多心力时间在学生身上的老师,实无异于一种几近消亡的文化遗产。
可堪告慰的是这一切无助于升职的劳动到底结下了纍纍异果,他的学生毕业之后依然不倦地阅读思辨,有的甚至接下其师的棒子,或者继续走上学者的路线(有学院派也有民间派),或者成为新一代学运中坚。
正好近日母校中文大学惹起风波,人人关注大学的价值与学运的未来,于是我有理由找周保松叙旧细谈。
梁: 梁文道
周: 周保松
梁:最近《南方周末》转了封读者来信给我,因为现在内地快要高考了,学生们都在考虑填志愿、选择科系。他们挑选了一些有关的问题,请我们一班作者去回答。其中交给我的问题是:有一位中学生,他很想读哲学,但是他的家人和老师都反对,觉得读哲学没有前途,赚不到钱。这位学生很困扰,不如你教我怎么回答他吧。
周:每年都有其他学系的学生来找我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刚接触哲学时,很多人都会着迷,与我们当年一样。那些问题很有趣、很贴身,重视生命的人一定会去想这些问题,所以他们一旦接触到这些问题,就想转去哲学系。问题是他们要面对家里和整个社会的压力,在一个不是很肯定intellectual的生活的世界里,这种追求实在很难。
梁:在《相遇》这本书里,你担心你教书的时候与你的学生提出很多与社会主流不同的价值观和反省;但学生出去了,还是需要在一个主流的社会中找工作,那你是帮了他们还是害了他们呢?但你的一个学生反而质疑你怎会这么说,因为他觉得在这三年中的获益很大。那是08年写的一篇文章,现在回看,你还有这种困扰吗?
周:困扰一定是有的。学生自己会来跟我讲,他们毕业了到社会上工作,一定会面对种种张力,但我们觉得这是值得的。教育是一个empowerment的过程,我们叫做充权,它增加你的自信、扩阔眼界,然后你会看到另外一些可能性,你看到生命或生活原来有另外一些possibilities,于是你就会有改变的力量了。如果整间大学都可以这样为学生充权,都可以培养学生对哲学和对社会的兴趣与关怀,就会慢慢形成一个力量了。就像我的学生,有人毕业后到中学做通识教育老师,我觉得这就是好的影响。不用太悲观,觉得一出去就没有自己、没有选择。我一直不想那么快就跟学生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主流没得抗拒这类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没到这个地步,那么快就将自己的自主性放弃。当然有张力、有压力,但你该问自己要如何在这么大的限制下去过一个较自主的生活、一个自己追求的生活。
梁: 说到这种张力,我甚至一直觉得,一个真诚的人一定会永远感觉得到这种张力。如果有人觉得没问题,那他不是圣人,就是傻子。因此他们难免会觉得难过痛苦。你的学生当中有没有这种经历呢?会不会觉得出去工作很辛苦呢?
周:一定有。我们的学生面对他们的选择,一定要为自己做决定。你看到不同的人正在走不一样的路,有的学生比较清楚,比较知道自己想要怎么的生活。我们政治学系的学生有些想做公务员、有些想做AO、有的走抗争的路、有的继续升学。大学教了最基本的东西,你令他们自己思考,但最终选择哪条路仍然是自己要负责。
梁: 我知道你与学生开了一些很热闹的网上讨论组,在我看来是做了很多大学规定之外的东西,甚至是今天的大学教授不应该去做的事情。可以说说这些讨论组的运作是怎样的吗?
周:每开一门课程,我们就开一个讨论组,除了平时上lecture、上tutorial之外,大家还会持续在网上廿四小时互相交流。其用量惊人,通常一个学期、两三个月下来就累积了几十万字,学生一直active地参与讨论,而且讨论也不限定于课堂所学的,也可以是人生哲学的问题和其他社会上发生的许多事情。讨论之后有些行动他们还会跑去参与实践。像反高铁那时,就有学生去参与运动;最近的五区公投也有学生去参选,由其他学生助选。我觉得这是要将学问和生活融为一体,因为读政治最难的是一种政治感,the sense of politics,你要感受到政治对你的生活、整个社会的重要性,而不只是觉得政治是一种抽离的技术性概念。
另一个讨论组我叫做「政治哲学与人生」。这是每年我教完一门课,让一些读完这个course之后还想继续这种知性的讨论的学生进来。这里长期有些不同界别的学生组成一个community,现在共有三百多人,维持了六、七年。
梁: 你回来教书教了八年,一回来没多久就开始做这件事。为甚么?
周:大家都知道哲学最重要的就是对话、讨论,你要敢于表达你自己的观点与意见。我经常鼓励他们,最好的思想training就是将自己的观点讲出来,接受其他人的批评、接受其他人的挑战。习惯了之后,这正好是cultivate一个民主公民的最好途经。最近一年半载,看到我们同学的文章登上报纸,就可以看到这个training的效果。这是真正的 life long learning,终身学习。其实有很多学生都毕业好多年了,但都还坚持看论文和评论文章,关心中国、关心国际,然后他们可以自由讨论。这个过程就是让他们觉得不那么孤独,因为毕业后单打独斗是很辛苦的,尤其发觉你做的事与身边的人都格格不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没有力量。但如果有一个platform,便知道很多人都在关心同一件事,你想的不是一些另类或没人支持的事。
梁: 除了这些网上群组,你好像还搞了一个「犁典读书组」?
周:我不敢肯定这个读书组是不是全港维持得最久的一个,它至今也有六、七年了,一直都能保持十几个人,现在有些人去了Oxford读书,有人走也有人进来,成员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一些老同学老朋友。我们每次因应一些不同主题,挑选最重要的相关文章展开讨论。例如香港正在讨论民主化,所以我们接下来会读一些和 democracy有关的原典。我们两、三个礼拜聚一次,每次谈三、四小时,持久地读下去,很严肃地一起聊,慢慢累积下去,大家以后或者就会成为整个公民社会中重要的参与者。
梁: 你教书要备课,还要写论文、做研究,你有时间吗?
周:在现有的大学体制中做这些事,其实是大傻瓜,这是真的,完全没有分数计算。所以这也是大学教育的危机。你看到现在的大学是千方百计将老师赶离学生。在你的升迁、续约考虑里面,只看你的publications;至于你放多少时间在学生身上,体制上是毫不关心的,甚至告诉你别放太多时间在学生身上,因为这样对你是很不智的。当然你说学校会有course evaluations,每份evaluation都有十几条问题,但是他们只看两条,就是「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course?」及「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lecturer?」这两个问题会化成数目字,比如1至6,非常满意至非常不满意。
所谓的重视教育其实是一个数字,中间所有其他东西都不见了。而你和学生的交流、学生的转变,这些教育最核心的部分在整个assessment当中都不见了。在现代那些国际大学不同的ranking里面,这些部分也是没有的,最多只能看得到一个师生比例,完全没办法evaluate一个teaching quality,譬如师生关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提升了多少等等。这些完全在所谓ranking或calculation中消失了。结果所有老师都不被鼓励关心这些事了,连老师都不做老师,教育的本义就无法继续下去了。香港在讲民主化,中国在讲如何改革,我们正面对一种政治转型;而政治转型是需要有人去推动的,那我们需要甚么人材去推动?这是整个大专教育应该要想的问题,但奇怪的是,整个大专教育似乎没有想过要去培养甚么人去推动社会改革。
梁:目前全世界基本的趋势就是,大学是整个社会经济未来动力的发动机或培育所。例如有些生化学科就和药厂合作研究,甚至已经到了违反学术伦理的地步了。因为大学里的研究是应该拿出来登在学刊中公诸天下的,但现在很多研究都不公开,他帮药厂做、要注册专利,又怎么可以公开呢?人文学科只是聊备一格,当学校已经变成这样子的时候,不谈你刚才讲的那些问题反而是正常了。
周:教育商品化当然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意识形态扩张,将市场的逻辑应用在教育的领域当中。借用Michael Walzer讲的Sphere of Justice,教育本身应该是一个独立的sphere,有它自己内在的价值与伦理规范。现在你用市场的逻辑入侵大学的时候,整个大学就会跟着市场的模式去运作,用资本主义的逻辑去运作。那结果当然会将传统大学的理念边缘化,像我们说的那些价值。我们以前讲教育,可能除了追求真理之外就是德性的培养,或是现在讲的民主公民价值,一个民主社会应具备甚么样的civic virtues,这些我们以前都看得很重。还有全人教育的目的是将人的本性和potential发展出来,从而有助于人实现他的well being。也就是说,传统大学教育离不开个人人生计划的实现,以及在一个政治社群中做一个好公民,从而令整个政治社群可以得到改善。但你要是将它变成一间公司、一个企业,当然它最重要最大的目标就只是帮市场培养它需要的人才。所以你现在见到一间excellent的大学最重要是看僱主满不满意它生产出来的产品。
如果你认为大学只是去满足既有制度的工具,那它便会失去批判性了。如果连大学都失去批判性的话,社会便没有其他空间和知识资源去对我们既有的制度做出一些挑战,或者引导社会去看到其他的可能性了。像这次的金融风暴,很多大学好像完全没有反省过自己在这个危机中需要承担甚么责任,更不会问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很失败。整个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是那些所谓的精英过度贪婪,没有最基本的操守和社会伦理。问题是这些所谓社会精英是哪里培养出来的呢?就是我们所谓最好的大学。即使哈佛或美国最顶尖的大学都已经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了,这条路是不是走错了呢?大学是不是应该有自己的一条路然后抗衡这个所谓的市场逻辑?这是我们需要去想的。
梁:我知道现在的大学要求教授出很多paper,把注意力从学生身上移开了。但回想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不也整天都说有很多老师不做研究吗?根据那种德国研究型大学的理念,教学应该相长,你做了研究,才有东西拿出来教学生。所以,这岂不是过去几十年香港认真的大学生所期盼的事?
周:教学与研究在理念上是没有冲突的,而且我觉得应该两者兼重,能平衡是最好的。但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时间就只有这么多,你多放一分钟时间在学生身上,你就没可能将所有精力放在另一边。所以下一步我觉得应该考虑两件事,第一就是校方能否提供一个较好的环境去肯定教学的重要。第二就是你所说的研究到底是做甚么研究呢?现在的研究往往重量不重质,不断催谷老师去申请research funding,然后用那个funding来衡量研究的成就。你要问一个好的研究、高质素的研究,要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下才能产生出来?譬如你讲哲学,John Rawls 五十岁才出他的第一本书,但一出便是经典。不同学科有不同性质,不同老师有不同的特长和不同研究的路向,可能有些东西是要厚积薄发的,例如以前的中央研究院甚至规定研究员进去头三年不能出论文。好的教育需要很长时间来跟学生相处,好的研究则需要很长时间去累积和develop 。
梁: 所以当代学者只出论文集,而专著则几乎消失了。
周: 在现在的评核制度中,一本书等同一篇论文,那还有谁会去写书呢?而且写一本书可能需要十年八年,一个真正的好学者一生可能就只出一本书。在现在这个学术环境中,这一类学者可能就无法生存了。
梁: 又以我们中文世界的学者为例,可能他写专著时想用中文,但它的分数一定比一篇英文论文低。
周:甚至完全不被承认,现在这种情况很普遍。只要你用中文写作,不理内容是甚么、不理它有多重要,只要是你用中文去写,就不会被承认。我想不到有比这更荒谬的情况。语言是需要develop需要累积的,我们没办法去发展自己的学术语言。如果我们没办法去发展学术语言,就没办法用自己的学术语言去思考社会问题了。我们正面对一个这么大的时代,中国有那么多问题,我们不用自己的语言和框架去思考这些问题,提出我们的反思,然后将我们香港所有大学的所有精力完全放在另一边,那其实是辜负了整个社会对大学的期望。我们身上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将学术语言中文化,将这些概念框架慢慢累积起来。你想想我们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整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其实也就是从翻译做起,然后民主和自由等概念才能引入中国社会。所以我在大学经常讲要肯定中文学术、重视高水平翻译的重要性。如果不做这些事情,我们中文的学术水平没办法成长,而我们社会的发展速度又远远超过学术圈的理解能力,那我们就永远是摸着石头过河,永远没一个自己的理论框架去了解社会发生了甚么事 。
梁:你刚才提到的那种大学理念十分传统,但这个理念到了韦伯的时候已经体现出一些矛盾的地方了。因为它强调通识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s,要让学生变成一个较完整的人,要让他去分享这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要让他对自己的人生多些反省,得到一个比较幸福的人生。但这套东西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而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在现代已经有危机了。因为在价值多元的世界里面,大学要不要价值中立呢?人文主义的价值本身是否也是一种价值?而且从前那种对人的想法在现代世界是否仍然合理呢?
周:我与石先生也谈了很多这类问题,你知道他对现代社会的想法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多神主义。在这么一个所谓价值主观主义、价值怀疑主义甚至价值虚无主义的时代,你还能不能讲一些大学的理念、坚持一种大学的价值呢?我承认这是一个蛮大的问题。而我初步的想法是:第一,根本没有所谓中立的大学,即是说无论你喜不喜欢,你办一所大学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我觉得没有所谓neutral的大学,neutral背后都有一个没讲明的立场或态度。
既然没有所谓价值中立的大学,那么我们面对不同的大学理念,自然就要追问哪一种理念最合理。简单说,你办一所大学,自然要问你想教学生甚么?你想他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每一个学生也要自问我怎样透过教育令自己活出一个好的人生。不管你是甚么主义,你都需要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些有理据的答案。我不觉得有所谓的唯一理想大学,只是拥有不同观念的人需要各自提供理由。
我觉得它不外乎两个基本的问题,第一,我们需要有一个对人的理解,即是说人是甚么,甚么构成一个good life?用回古典希腊的说法,这是个How should I live的问题。第二个则是How we live together 的问题,因为大学是一个社会,接受公帑,所以除了问自己可以如何得到一个好的人生外,亦要关心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共同生活。由此引申,我们便需要理解大学在社会中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梁: 照你刚才的说法,大学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那你怎么看最近中大的民主女神像事件?校长刘遵义很强调「政治中立」,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价值问题,跟「政治中立」无关。
周:政治中立是应用在校方上的,因为它拥有权力,当它去决定一些大学事务的时候,譬如老师的升迁、研究课程的设计和学生活动的时候,它不能够诉诸一些政治的理由来作为判断的依据。因为这有助保障一个兼容并包及自由开放的校园,容许教师和学生去自由探索、自由辩论。但这个意识本身并不是中立的,政治中立本身不是一个中立的原则,它其实有一个价值协定,协定大学要把持兼容并包的立场。把这个层面弄清楚之后,就回到你那个「六四」的问题。其实我们是在问另一个问题:究竟大学作为一个公共机构,它有没有一些最基本的价值坚持?一定要有的。我想没有人否认大学有两个最重要的角色,第一,它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已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坚持,这意味着你不能容忍一些虚假的东西,你要接受真相;譬如你说「六四事件」,你便要承认那是一个怎样的事实。第二,你除了追求真理,还要把持公义。当然,公义的内容是甚么是有讨论余地的,可是大学有一个责任,就是它是社会的一部分,大学要培养好公民,好的公民当然会把持公义,不然我们培养这批人出来做甚么呢?你能想象德国大学在面对纳粹的时候还说甚么中立吗?这根本不合逻辑。你接受人人平等的理念,你就要接受德国的公民不能因为他的种族和宗教而被歧视伤害。
所以这里有两个层面,第一,大学对我们整个社会共有的高度共识协定是不能放弃的,那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底线。譬如反对种族歧视、政府不能屠杀人民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长远历史之中早有共识的东西,构成了整个民主社会的基础。第二,即使某一所大学所说的价值不是如此普世性,但我们也会尊重某些大学和学院有它自己的价值坚持,只要它的坚持没有破坏一些社会的基本原则——例如你可以宣扬基督教,但基督教学校不能压制其他学校的信仰,就像崇基和新亚,大学容许它们有自己的理念,但同时尊重学生们有追求其他信仰的自由。
梁: 他们在声明内说,为了保证学术自由,其实学术自由已经是价值选向。
周: 对。
梁: 如果照这个说法,你该认为中大用「政治中立」的理由去拒绝放置民主女神像是非常不恰当的。
周:假若以政治中立原则作为它的前提的话,推论出来的结论应该是容许学生摆放女神像,而不是不准许。他顶多只能说学生的立场不等于校方的立场,这样他的立场就比较一致。当然,下一步或许有人会说,他不只要让学生摆放,更要肯定学生的行为,这就像你刚才说的,校方是否该超越政治中立的原则,而去肯定某些普世价值。我认为这是两种层次,即使从内在的角度,从他自己肯定的政治中立原则,也推论不出它现在的结论。
梁:大家都在说中大的传统,有趣的是不论崇基或新亚,甚至联合,这三家早期建立中大的学校背后均有一种对中国的承担。恰好现代大学都是民族主义时期的产物,它们都把自己定位成national culture的捍卫者、发扬者。我们祖辈成立这间大学时心中也一定有一套民族文化,其中包涵了一些价值,但依据这些想法和精神而建立的这间大学在发展到后来的时候却会出现很多不同的声音,甚至可能正正就是要反对这种建立在与民族文化有关的大学理念。换句话说,一间大学的建校者有一个看法,这个看法背后有一种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主动承担,但到了后来,学生也好、老师也好,却可能会反对这种对文化民族的理解或承担。
周:这是另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先说几件事。第一,我觉得一间好的大学必须有一个悠久的传统,但这传统却不是不变或固定的,不是说甚么建校先贤定义了那种传统就等于整间大学的精神。我自己在中大经历了二十年,我们需要的不是一本圣经或先人的传统,然后我们就要死跟着它,觉得那是甚么甚么精神。我认为该有个创造性的诠释,一个有力的传统,是该容许一代一代的中大人去对你的传统诠释、建构、丰富。它愈丰富,这间大学就愈有活力,这丰富的过程是传统的一部分。
梁:套回中大的例子说明,无论是主张最原始的那种新亚精神,还是写大字报去骂新亚精神,对我来说也依然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一种对价值很积极的认定,一种肯认,一种承担,这是很重要的。中大五十年,无论你是哪一种学生运动,大家对价值有一个起码的肯认,绝非价值虚无主义。
周:我绝对同意,在中大四十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尝试去定义甚么是中大精神,那就是价值关怀和社会批判,它绝对不是中立,而且绝对愿意承认它对社会有承担,我认为这是中大最重要的资产。这次的事件好像对中大构成很大的伤害,但相反来看,有二、三千人护送女神像,有这么多人走出来,正是看到中大的价值意识和社会批判的存在。我能肯定地说,不只在香港,甚至在整个华人地区,也没有几间大学培养出这种传统和自我期许,这比竞争国际排名要有意思得多。
梁:一间大学对社会表达对它的关怀和承担,往往与学生运动有关。然而,学生运动也会留下很多问题。譬如说上世纪德国六十年代的学运,法兰克福学派本来是当时最有批判性的一群学者,却被学生骂保守,上课时还拿东西丢Adorno,那时Habermas说了两句我认为很妙的俗话,他说学运的矛盾就是你大学一年级进来,笨笨的,甚么都不懂;大学二年级,开始接手;大学三年级,整群人终于非常成熟了;大学四年级,你却即将离开,接着就毕业了。似乎学运注定不能持续,只能是一个很短暂、很短线的介入,它不能对某个议题某个阶级有一个很长期的关注。
周:学生角色尴尬的地方是他们在大学内是一个过渡的角色,没办法持续地跟进一个问题,因为你只留在大学三年。但你看回过去的经验,中大培养了很大一群社会运动的生力军,于是学运和社运的传统便连结在一起了。很多学生搞过学运,出去之后便投入社运,你想想我们的时期:谭俊贤、蒙兆达和林英瑜,这些人仍然在社运前线。又譬如最近的「左翼21」、反高铁以及批判富士康,其实都有校友和在校生在互相配合。
梁:人类社会和文明的不停演化需要很多新观念,大学就是在孵育这些观念和技术。有一天要是人类要离开地球,那办法也多半是从大学里出来的;同样地,如果说大学是社会上各种观念的实验室,那么学运也一样有这种功能。Habermas 所说的缺点,我反而认为是强项。学生是甚么呢?学生是一群没有职业,不需要在社会上被嵌进一个固定工作位置,却很难得有三、四年时间自由浮动的实验者。所以学运往往会关怀一些跟学生距离很遥远的事情,你在英国肯定也看过那些关心巴基斯坦童工的学生吧。他们可以一下子关心这么遥远的人群,正正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一个有利的位置。故此学生更加要把握这段时候,摆脱任何以功利联系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创造最大胆的想象和最有趣的实验。
周: 大学最精彩的地方就是理想性和纯粹性。这是在你离开以后很难做到的。你说大学生不成熟、天真;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好处就是理想和纯粹,恰恰足以彰显世界上很多不理想也不纯粹的东西,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